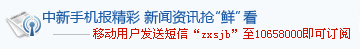АПЗ»ТХИЛПВҝа№ҰС§ТХ С§іӘ¶ФЧЕЛ®әИДт»ӨЙӨ(ЧйНј)(3)
ЎЎЎЎіҫ·вөДҫзұҫәНЖӨУ°
ЎЎЎЎХвҙОөзКУМЁАҙІЙ·ГЈ¬10¶аГыАПЗ»ТХИЛҫЫФЪТ»ЖрЕЕСЭАПЗ»Ј¬ЙгПс»ъПФСЫөШјЬЧЕЈ¬ҙеЧУАпИҙБ¬Т»ёцҝҙИИДЦөД¶јГ»УРЎЈёйФЪТФЗ°Ј¬ХвКЗІ»ҝЙПлПуөДЎЈ
ЎЎЎЎөұКұҙеЧУАпјёәхЎ°ИЛИЛ¶ј»біӘјёҫдЎұЎЈТ»іӘЖрАҙҫН»бУРИЛФъ¶С¶щЎЈПДМмНнЙПГ»КВөДКұәтЈ¬јёёцИЛҙХФЪТ»ЖрЈ¬ЛӯТӘЖрәеЛөХыЙПТ»¶ОЈ¬ҫН»бУРИЛіӘЙПДЗГҙјёҫдЎЈХЕЛДјҫОӘҙЛ»№өГөҪ№эјё°ьСМөДҪұАшЎЈЛыГҝіӘЙПТ»¶ОЈ¬ҫН»бУРИЛёшЛыВт°ьСМЎЈ
ЎЎЎЎГыХрТ»КұөДАПЗ»ТХИЛХЕИ«ЙъөД№ККВЈ¬ИзҪсјҙұгФЪЛ«ИӘҙеТІПКУРИЛЦӘөАЎЈЙПКАјН40ДкҙъіхЈ¬УРИЛАҙЗлХЕИ«ЙъөДП·ЎЈЛыТтјТАпУцКВІ»ПліцГЕЈ¬ҫНҪиҝЪГ»УРІсЙХБЛЈ¬ЧФјәТӘИҘҙтІсЎЈ¶Ф·ҪМэәуЈ¬ҫ№УГ3Н·ВвЧУҪ«ІсҙУ70АпНвЛНөҪХЕјТЎЈХЕИ«ЙъІ»өГІ»Б¬Т№јжіМЈ¬ёПөҪ¶Ф·ҪјТАпіӘП·ЎЈ
ЎЎЎЎАПЗ»ТХИЛЦР»№Бчҙ«Т»ёц№ККВЎЈГс№ъКұОч°ІіЗЦРУРИЛЗлАПЗ»ТХИЛіӘП·Ј¬Н¬Кұ»№ЗлБЛіӘұрөДП·ЦЦөДјёёцП·°аЧУЎЈНнЙПЎ°¶ФМЁЎұКұЈ¬АПЗ»ЖӨУ°П·МЁЗ°өДИЛБИБИОЮјёЎЈө«АПЗ»Т»іцЈ¬ВнЙПОьТэБЛәЬ¶аИЛ№эАҙЎЈәуАҙИЛФҪҫЫФҪ¶аЈ¬ЦВК№П·МЁЗ°І»Ф¶өДТ»¶ВО§ЗҪ¶јұ»ј·ө№БЛЎЈ
ЎЎЎЎЎ°ДЗКұҝҙП·өДИЛәЬ¶аЎЈУРөДИЛЙхЦБТӘЕЬјёК®АпВ·ёъЧЕҝҙЎЈУРКұТ»ұҫП·іӘНкЈ¬МЁПВөДИЛ»№ТӘЗу¶аіӘјёёцХЫЧУП·ЎЈЎұ»ШТдЖрөұКұөДЗйҫ°Ј¬ХЕПІГсРҰіцЙщАҙЎЈ
ЎЎЎЎХЕПІГсұЈБфУР50УаұҫҫзұҫЎЈХвР©ҫзұҫұ»№ьҪш°ьёӨЈ¬·ЕФЪөзКУ»ъПВөДТ»ёц№сЧУЦРЈ¬ПЦФЪәЬЙЩДГіцАҙЎЈЛыөД°аЙз»оФҫКұЈ¬ЛыіцГЕЧЬТӘҙшЙПХвР©ҫзұҫЈ¬ОЁҝЦКВЦчјТөгөҪЧФјәІ»КмПӨөДП·ЎЈЖдКөЈ¬ЛыІ»ҝҙҫзұҫТІДЬіӘіцК®¶аұҫП·ЎЈ
ЎЎЎЎПЦФЪЈ¬ЛыјёәхБ¬Т»ұҫТІјЗІ»И«БЛЎЈёъЧЕөі°І»ӘЕЬ¶«ЕЬОчЈ¬ЛыУГІ»ЧЕ·СЙсјЗҫзұҫЎЈјҙК№КЗЕЕСЭҙ«Ні¶ОЧУЈ¬ТІЦ»УГЖдЦРөДТ»РЎІҝ·ЦЈ¬ГҝёціӨ¶ИІ»№эјё·ЦЦУЎЈ
ЎЎЎЎЛыГЗөДёёұІЎўЧжұІЈ¬КУҫзұҫәНЖӨУ°ОӘұҰұҙЎЈДЗКЗЛыГЗөД·№НлЈ¬¶ӘБЛХвБҪСщЈ¬ҫНөИУЪФТБЛ·№НлЎЈ
ЎЎЎЎГс№ъКұөДАПЗ»ТХИЛХЕУсУЎ»јІЎЗуТҪЈ¬¶ФНвіЖДЬЦОәГЛыөДІЎХЯЈ¬Ҫ«»сөГИ«ІҝөДАПЗ»ҫзұҫЎЈТ»ИЛҪ«ЖдІЎЦОәГәуЈ¬ХЕУсУЎУЦЙъ·ҙ»ЪЎЈҙОДкЈ¬ХЕУсУЎФЪТ»ёцҙеЧУСЭіцКұЈ¬ЦОәГЛыІЎөДИЛёъЛж¶шЦБЎЈіГП·СЭНкІрМЁЧУЦ®КұЈ¬ҙЛИЛҪУЧЎБЛҙУМЁЙПөЭПВөДҫзұҫ°ьёӨМУЧЯЎЈұЁ№ЩәуЈ¬ХЕУсУЎІЕЧ·»ШҫзұҫЎЈө«ҙЛЖЪјдЈ¬П·ұҫТСұ»ИЛМЬіӯТ»ұйЎЈЦБҙЛЈ¬АПЗ»№гОӘБчҙ«ЎЈ
ЎЎЎЎЎ°ОДёпЎұЖЪјдЈ¬Л«ИӘҙеөДАПЗ»ТХИЛОӘұЈҙжҫзұҫЈ¬ЖД·СРДЛјЎЈХЕПІГсөДёёЗЧНөНөФЪЧж·ШЕФНЪБЛТ»ёц¶ҙЈ¬Ҫ«Ч°УРҫзұҫәНЖӨУ°өДП·ПдІШФЪ¶ҙЦРЎЈУРКұ°лТ№ИэёьЈ¬Лы»№»бЖрҙІөҪ·ШөШҝҙҝҙП·ПдКЗ·с»№ФЪЎЈ
ЎЎЎЎХЕЛДјҫөДёёЗЧФтФЪјТЦРҪшГЕөДөШ·ҪНЪТ»ёцҙу¶ҙЈ¬¶ҙЦР·ЕБЛТ»ҝЪҙуЛ®ёЧЈ¬Ҫ«П·Пд·ЕҪшЛ®ёЧәуЈ¬ФЩФЪЛ®ёЧЙПёЗБЛТ»ҝйКҜ°еЎЈКҜ°еЙПөжЙПНБЈ¬ЧоәуУЦ°СөШёҙФӯЎЈәмОАұшАҙіӯјТКұЈ¬ЛыЧјұёБЛТ»Р©ЖЖЛрөДҫзұҫәНЖӨУ°Ј¬Ҫ»іцБЛКВЎЈ
ЎЎЎЎҙеАпЧоФзөДҫзұҫКЗЗ¬ВЎДкјдөДЈ¬ФЪХЕРВГсКЦЦРЈ¬ЛыКЗГыҪЗХЕИ«ЙъөД¶щЧУЎЈИзҪсЈ¬ЛыөДҫзұҫТІГ»ФЩ·ӯ¶Ҝ№эЎЈЛы»№УР100¶аёцЖӨУ°ЙнЧУТФј°500¶аёцЖӨУ°Н·Ј¬ө«ХвР©ЖӨУ°Ј¬јРФЪУІЦҪ°еЦРЈ¬ұ»ІгІг°ь№ьЧЕЈ¬ТІУРәЬіӨКұјдГ»ИҘ¶Ҝ№эБЛЎЈ
ЎЎЎЎХЕПІГсөДБҪёц¶щЧУЈ¬Г»УРТ»ёцС§ЛыөДКЦТХЎЈө№КЗЛыөДТ»ёцРЎЛпЧУЈ¬Еј¶ыДЬіӘЙПјёҫдЎЈө«ЛыІўІ»ЦчХЕЛпЧУҝҝХвіФ·№Ј¬Ў°УйАЦУйАЦҫНРРЎұЎЈ
ЎЎЎЎ2006ДкЈ¬ХЕЛДјҫёъЧЕөі°І»ӘөҪұұҫ©СЭіцЎЈ»ШАҙөЪТ»јюКВҫНКЗ°СЧФјәөДЛпЧУҪР№эАҙЈ¬ҪМЛыіӘАПЗ»ЎЈЛпЧУіӘБЛДЗГҙјёҫдЈ¬ХЕЛДјҫёРҫхРДАпКжМ№БЛЎЈІ»№эЧоЦХЛпЧУТІГ»ёъЧЕЛыС§П·ЎЈ
ЎЎЎЎДҝЗ°Хыёц»ӘТхЈ¬ДЬіӘАПЗ»өДІ»№э20УаИЛЎЈДкјНФЪ40ЛкТФПВөДТХИЛЈ¬јёәхГ»УРИЛДЬіӘұҫП·ЎЈ
ЎЎЎЎ°ЧГ«әНХЕПІГсҪьДкКХБЛІ»ЙЩНҪөЬЎЈЛыГЗТІПлҪМХвР©НҪөЬГЗіӘИ«ұҫП·өДАПЗ»Ј¬ҝЙКЗГ»јёёцФёТвС§ЎЈ
ЎЎЎЎЎ°АПЗ»ПЦФЪ»рБЛЈ¬әЬ¶аИЛ¶јКЗіеЧЕХвёцАҙөДЈ¬ПлПЦС§ПЦВфЎЈЎұХЕПІГсЛөЎЈ
ЎЎЎЎІ»№эЈ¬ХвР©Ц»С§БЛЖӨГ«өДНҪөЬГЗ№эөГТІІ»ҙнЎЈЛыГЗұ»өі°І»ӘХыұаөҪБнНвТ»ёцНЕ¶УЈ¬ДГЧЕ№М¶Ё№ӨЧКЈ¬ФЪ»ӘЙҪҪЕПВТ»ёцСЭТХМьСЭіцЎЈ
ЎЎЎЎКөјКЙПЈ¬Ҫь800ИЛөДЛ«ИӘҙеАпјёәхҝҙІ»өҪ¶аЙЩДкЗбИЛЎЈЕјУРјёёцДкЗбИЛЈ¬ҫщұнКҫІ»ПІ»¶ҝҙАПЗ»ұнСЭЎЈТ»ёц40ЛкіцН·өДҙеГсЛөЧФјәКЗҙеАпЛШ№Д¶УөДТ»ФұЈ¬ө«ТСҫӯәЬіӨКұјдГ»УРЗГ№эБЛЎЈ
ЎЎЎЎГ»ПлөҪ№ЕАПөДЕ©ҙеТЎ№цТІТ»СщКЬ»¶Уӯ
ЎЎЎЎ11ФВ7ИХФЪОч°ІөДСЭіцЈ¬ХХҫЙКЗАПҪЪДҝЎ¶ЙВОчК®ҙу№ЦЎ·Ј¬МЁПВХХҫЙКЗАЧГщ°гөДХЖЙщЎЈСЭНкәуЈ¬УРИЛМбТйіГФзБпЧЯЈ¬І»ұШөИНн»бҪбКшЎЈ
ЎЎЎЎЎ°Г»ТвЛјЎЈІ»ИзФзөг»ШјТЛҜҫхЎЈЎұТ»ГыАПЗ»ТХИЛЛөЎЈ
ЎЎЎЎ»ШіМВ·ЙПЈ¬ЛыГЗҝӘКјМЦВЫТ»Р©әНЛыГЗөДЙъ»оАлөГТЈФ¶өДОКМвЎЈұИИзЈ¬ЛыГЗМЦВЫ·Ё№ъЗ°І»ҫГ·ўЙъөДУОРРЈ¬МЦВЫјҙҪ«ФЪ№гЦЭҫЩ°мөДСЗФЛ»бЈ¬МЦВЫГА№ъёХёХФцУЎөД6000ТЪГАФӘЈ¬МЦВЫМЁНеИЛөДЙъ»оЎЈ
ЎЎЎЎЎ°ОТҫхөГМЁНеИЛ»оөГІ»РТёЈЎЈҙуҪЦЙПҝҙІ»өҪТ»ёцПРЧЕөДИЛЎЈУРөДИЛ¶јАПБЛЈ¬»№ФЪ№ӨЧчЎЈДДПсОТГЗЈ¬АПБЛҫНКІГҙ¶јІ»ёЙБЛЎЈЎұУРИЛЛөЎЈ
ЎЎЎЎЎ°ОТГЗ¶јТСҫӯАПБЛЈ¬І»ТІХХСщЕЬАҙЕЬИҘЈҝЎұБнТ»ИЛ·ҙІөөАЎЈ
ЎЎЎЎЎ°ОТГЗКЗПлёЙҫНёЙЈ¬І»ПлёЙҫНҝЙТФРӘЧЕЎЈЎұХвұЯІ»·юЖшЎЈ
ЎЎЎЎЛ«·ҪХщЦҙІ»ПВЎЈУРИЛҙтФІіЎЈ¬БҪИЛІ»ЛөБЛЈ¬УЦі¶өҪұрөД»°МвЎЈ
ЎЎЎЎХвР©ДкЈ¬өі°І»ӘҙшЧЕХвИәАПЗ»ТХИЛЈ¬ҙУ»ӘТхЧЯПтИ«№ъЈ¬ЙхЦБ»№Ф¶¶ЙЦШСуЈ¬өҪИХұҫЎўГА№ъөИөШСЭіцЎЈ
ЎЎЎЎИҘДкФЪГА№ъСЭіцКұЈ¬ЛдИ»УпСФІ»НЁЈ¬ДЗР©ёЯұЗЧУА¶СЫҫҰЎўҙ©ЧЕАс·юЎўҝҙЖрАҙОДЦКұтұтөДАПНвЈ¬»№КЗТ»ҙОҙОҪ«ХЖЙщәН»¶әфЙщЛНёшХвР©ЙВОчөДЕ©ГсЎЈ
ЎЎЎЎөұКұЈ¬өі°І»ӘОӘКЗ·сҙтЧЦД»УлГА№ъөДЦчіЦИЛХщЦҙІ»ПВЎЈЧоәуіРСЭ·Ҫҫц¶ЁЈ¬І»ТӘЧЦД»Ј¬ТӘөДҫНКЗТ»ЦЦО¶¶щЎЈСЭіцҪбКшәуЈ¬өі°І»ӘНЁ№э·ӯТлёъҫзФәөДҫӯАнҝӘНжРҰЛөЈәЎ°ОТТФОӘХвЦЦҙуҫзФәЦ»ЙПСЭёЯСЕТХКхЈ¬Г»ПлөҪЈ¬№ЕАПөДЕ©ҙеТЎ№цТІТ»СщКЬ»¶УӯЎЈЎұҫӯАнРҰЧЕЛөЈәЎ°»¶УӯФЩАҙЈ¬»¶УӯФЩАҙЎЈЎұ
ЎЎЎЎГА№ъЦ®РРЈ¬ХвР©ТХИЛГҝИЛөГөҪБЛ220ГАФӘЎЈХЕПІГсҪ«ХвР©ГАФӘИ«¶јІШФЪТВПдАпЎЈЛыөДёзёзХЕЧӘГсЈ¬ФтёшБҪёцәўЧУТ»ИЛТ»°ЩГАФӘЈ¬ЧФјәБфПВ20ГАФӘЈ¬Ў°ЧцёцјНДоЎұЎЈ
ЎЎЎЎХЕПІГсПЦФЪЦ»УРТВПдЈ¬П·ПдФзҫНұ»ЛыИУөфБЛЎЈө«ЛыИФҫЙјЗөГП·ПдөД№ККВЎЈУРТ»ҙОПВҙуС©Ј¬ЛыөД°аЙзҙУЦРОзҫНіц·ўЈ¬ЧЯВ·өҪТ»ёц30¶а№«АпНвөДөШ·ҪСЭП·ЎЈёПөҪКВЦчјТәуЈ¬ТСҫӯНнЙП8өг¶аБЛЎЈКВЦчәЬІ»ёЯРЛЈ¬Г»ИГЛыГЗіФ·№Ј¬ҫНұЖЧЕЛыГЗҝӘіӘЎЈ
ЎЎЎЎ¶цЧЕ¶ЗЧУіӘБЛТ»іцұҫП·әуЈ¬КВЦчІЕИГЛыГЗіФЙП·№ЎЈ·№әуЈ¬КВЦчУЦТӘЗуЛыГЗҪУЧЕФЩіӘТ»іЎЈ¬І»И»ҫНҝЫПВП·ПдІ»»№ЎЈНт°гОЮДОПВЈ¬ЛыГЗЦ»әГјУСЭБЛТ»іЎЎЈЦұөҪҙОИХБиіҝЈ¬ЛыГЗІЕФЪТ»ёцГ»УРЙъ»рөДОЭЧУАпРЎЛҜБЛТ»»б¶щЎЈ
ЎЎЎЎХвјёДкЈ¬АПЗ»ТХИЛГЗөДЙъ»оҙҰҙҰ¶јКЗұд»ҜЎЈФЪЛ«ИӘҙеЈ¬ЧФ№ЕТФАҙТ»ДкЛДјҫ¶јКЗБҪ¶Щ·№ЎЈЙПОз10өг№эіФөЪТ»¶ЩЈ¬ПВОз4өг¶аіФөЪ¶ю¶ЩЎЈПЦФЪЛыГЗіцИҘСЭіцЈ¬Т»ИХИэІНЎЈУРКұОз·№КЗЧФЦъІНЈ¬ІЛЖ·І»ЙЩЈ¬ө«УРИЛРЎЙщұ§Ф№·№ІЛДСіФЎЈ
ЎЎЎЎЛыГЗФЪұұҫ©СЭіцКұЈ¬Т»ГыФЪҙЛЗуС§өДЙВОчј®С§ЙъФш¶аҙОёъЧЕЛыГЗҝҙСЭіцЎЈәуАҙЈ¬Лы»№ЧЁіМөҪ»ӘТх№ЫҝҙұнСЭЎЈУРТ»ҙОЈ¬Лы¶Фөі°І»ӘЛөЈәЎ°өіөјЈ¬ОТ·ўПЦБЛТ»ёцОКМвЎЈХвР©АПЗ»ТХИЛҝӘКјМфМЮ·№ІЛөДЦКБҝЈ¬ҝӘКјМфМЮҫЖөкКЗ·сКжККЎЈІ»ЦӘөАХвСщПВИҘЈ¬ЛыГЗКЗІ»КЗФЪСЭіцКұ»б¶ӘөфТ»Р©ЦКЖУәНҙҝҙвЈҝЎұ
ЎЎЎЎөі°І»ӘөД»ШҙрКЗЎ°УҰёГІ»»бЎұЎЈө«ұд»ҜЦХ№йКЗДСТФұЬГвөДЈ¬ХвҙУЛыГЗГж¶ФөзКУМЁҫөН·КұөДұнПЦЦРҫНДЬҝҙіцЎЈ
ЎЎЎЎЎ°ҙујТ¶јЧјұёәГЎЈЎұФЪҫөН·ПВЈ¬ХЕПІГсҙУИЭөШХРәфЧЕҙујТЎЈ¶шөЪТ»ҙОГж¶ФҫөН·КұЈ¬УРјЗХЯОКХЕПІГсЈ¬ДгҪсДк¶аҙуБЛЈҝХЕПІГс»ШҙрЈ¬ОТіФ№эФз·№БЛЎЈ
ЎЎЎЎЙгЦЖ№эіМЦРЈ¬ЛыГЗОӘДіИЛөДТ»ёцҙнОу·ўЙъХщЦҙЈ¬ДгТ»ҫдОТТ»ҫдЛөёцГ»НкЈ¬И«И»І»№ЛЙгПс»ъөДҫөН·Хэ¶ФЧЕЛыГЗЕДЎЈ
ЎЎЎЎРЭПўКұЈ¬ЛыГЗ»№КЗ»бҝӘҝӘ°ЧГ«өДНжРҰЈ¬¶ш°ЧГ«ЧЬКЗРҰ¶шІ»ҙрЎЈУРИЛТӘЗуЛыіӘ¶ОЛбЗъЈ¬ёшҙујТҪвҪвГЖЎЈ°ЧГ«ГҰ°ЪКЦЛөЈ¬Ў°ОТІ»»бЎұЎЈКВКөЙП°ЧГ«КЗ»бөДЎЈ
ЎЎЎЎҪсәуөДСЭіцЈ¬ХЕПІГсТАҫЙ»бХРәф»пјЖГЗТ·Т»°еЈ¬°ЧГ«өДЛ®СМҙь»№КЗ»бЙ·УРҪйКВөШөгЎЈ°аЧУЦРОЁТ»өДЕ®ТХИЛЎў53ЛкөДХЕЗпСЕЈ¬ТІ»№»біҜЧЕ№ЫЦЪРЯфцөШЕЧёцГДСЫЈ¬ЕӨјёПВЖЁ№ЙЎЈ
ЎЎЎЎЛыГЗ»бјМРшКХ»сХЖЙщЎЈөі°І»ӘТСҫӯОӘЛыГЗ°ІЕЕәГБЛЈ¬өҪОч°ІСЭіцЈ¬өҪұұҫ©СЭіцЈ¬ГчДк»№ҝЙДЬөҪГА№ъИҘЙМСЭЎЈ
ЎЎЎЎДЗР©Йў·ўіцГ№О¶өДҫзұҫЈ¬ДЗР©ұ»іҫ·вөДЖӨУ°Ј¬І»ЦӘәОКұІЕ»бұ»ФЩҙО·ӯіцАҙЎЈДЗР©ФЪЛӯјТГЕҝЪЛжТвөШіӘАПЗ»¶ОЧУөДјЗТдЈ¬І»ЦӘ»№ДЬІ»ДЬФЩПЦЎЈ
ЎЎЎЎТІІ»ЦӘөАЈ¬ФЩ№эТ»Р©ДкЈ¬ДЗР©УлАПЗ»ЖӨУ°УР№ШөДЛЧУпЈ¬ұИИзЎ°АПЗ»У°ЧУҪЪҪЪУІЎұЈ¬ұИИзЎ°АПЗ»У°ЧУҙуҝЪЕЙЎұЈ¬КЗІ»КЗ»№УРИЛГч°ЧЛьГЗөДТвЛјЎЈ
ұҫұЁјЗХЯ №щҪЁ№в
 ІОУл»Ҙ¶Ҝ(0) ІОУл»Ҙ¶Ҝ(0) |
Ўҫұајӯ:ЖСІЁЎҝ |
-
----- ОД»ҜРВОЕҫ«СЎ -----
- ЎӨАҘЗъЎ¶ДөөӨНӨЎ·ББПаВн¶ъЛы ¶«Оч·Ҫ№ЕАПОД»ҜјӨЗйЕцЧІ
- ЎӨМҪ·ГЎ¶ВкДЙЛ№Ў··ЗОпЦКОД»ҜТЕІъҙ«іРИЛ КШ»ӨГсЧеЦЗ»Ы
- ЎӨТФҙ«ІҘЙз»бС§КУҪЗМҪЛчЈәРВЦР№ъЕ®РФРОПуұдЗЁ
- ЎӨЖҜСу№эәЈөДЎ°СуГАәпНхЎұЈә°Сҫ©ҫзіӘёшКАҪзМэ
- ЎӨЛ«УпПаЙщУлЦЪІ»Н¬ЈәөұПаЙщУцЙПЎ°Нб№ыИКЎұ
- ЎӨҪхАрЎў·рПөЎў№ЩРы...НшВзБчРРУпіЙОД»Ҝ·ыәЕ
- ЎӨ№К№¬НЖіцЎ°іхС©ЎұөчБП№Ю НшУСЈәіш·ҝЦұҪУЙэј¶УщЙЕ·ҝ
- ЎӨөЪК®ИэҪм»ЖөЫОД»Ҝ№ъјКВЫМіЈәС§ХЯТФК«ёиҪІКцјТ№ъЗй»і
- ЎӨІ»ЙбВГ°ДҙуРЬГЁ»Ш№ъЈЎ°ДҙуАыСЗҪ«ЧвЖЪСУіӨ5Дк
- ЎӨАъКұ3ДкҝзФҪ33№ъ әЙАјДРЧУНкіЙөз¶Ҝіө»·ЗтЦ®ВГ
- ЎӨ·рВЮАпҙпЦЭ№ъјТІ¶»сҫЮтю іӨ¶Иі¬5ГЧМеДЪУР73ҝЕө°
- ЎӨёЈФӯ°®ЖҪ°ІІъПВ¶юМҘ АП№«ҪӯәкҪЬПІЙ№Т»јТЛДҝЪ(Нј)
- ЎӨјУДГҙуТ»ІсИ®Тт»б»ӯ»ӯЧЯәм »ӯЧчТСКЫіцУв231·щ
- ЎӨјУУНЗ№ОҙКХЛҫ»ъјЭіө¶шИҘ јУУНХҫЙПСЭҫӘ»кЛІјд
- ЎӨЖҜСу№эәЈөДЎ°СуГАәпНхЎұЈә°Сҫ©ҫзіӘёшКАҪзМэ
- ЎӨҪә¶«БТКҝБкФ°ИлҝЪА¬»шұйөШЎўНЈіөВТКХ·СЈҝ№Щ·Ҫ»ШУҰ
- ЎӨҪб»йВКҪөАл»йВКЙэ КЗ¶АБўТвК¶бИЖр»№КЗ·ҝјЫМ«№уЈҝ
- ЎӨНшәмДкРҪ°ЩНтЈҝКРіЎөчІйЈәҪц20%өДН·ІҝНшәмФЪЧ¬З®
- З°№ъјК°ВОҜ»бЦчПҜИшВнАјЖжКЕКА
- НјЈәёЯҫ«јвҫҜУГІъЖ·әНјјКхББПаҫ©іЗ
- НјЈә°ВОҜ»бЙПөДИшВнАјЖж
- УсКчөШХрФЦЗшТ»Т№·зС© ҝ№ХрҫИФЦұ¶јУјиДС(...
- НјЈәёЯҫ«јвҫҜУГІъЖ·әНјјКхББПаҫ©іЗ(2)
- НјЈәёЯҫ«јвҫҜУГІъЖ·әНјјКхББПаҫ©іЗ(3)
- НјЈәёЯҫ«јвҫҜУГІъЖ·әНјјКхББПаҫ©іЗ(4)
- НјЈәёЯҫ«јвҫҜУГІъЖ·әНјјКхББПаҫ©іЗ(5)
- НјЈәёЯҫ«јвҫҜУГІъЖ·әНјјКхББПаҫ©іЗ(6)
- НјЈәёЯҫ«јвҫҜУГІъЖ·әНјјКхББПаҫ©іЗ(7)
- ИХПөЖыіөЗ°ЖЯёцФВФЪ»ӘПъБҝҪь200НтБҫ Дж...
- ЎҫНјҝҜЎҝГъјЗАъК· ДӘНьАПұш
- Ў°9.3ЎұҙуФДұшИ«БчіМЖШ№в Ў°ҪЪДҝөҘЎұЙП...
- №ъјКУНјЫРЧГН·ҙөҜ №ъДЪЖыІсУНјЫёсБщБ¬өш
- 30ЛкДРЧУВъБіЦеОЖИз80ЛкАПН· ТшРРИЎЗ®...
- °ЩЛкҝ№ИХАПұшҪҜДЬ
- әУДП500Д¶ЧҜјЪКХ»сФЪјҙұ»ЗҝІщ ИОРФИЗГсФ№
- Ў°ЧоұҜЙЛЧчОДЎұ·ўІјХЯТС»ШјТ іЖЦ»КЗЕдәПөч...
- ЦР№ъіөЖуұИСЗөПҙҝөз¶Ҝҙу°НББПа°НОчКҘұЈВЮіөХ№
- Ў°ПЦіЎЦёИПЎұұдЎ°УОҪЦКҫЦЪЎұ ПУ·ёИЁАыТӘІ»...
Copyright ©1999-2024 chinanews.com. All Rights Reserv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