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m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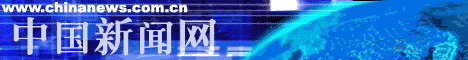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"�վ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ǡ��վ��ӡ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Ȳ����úܶ���֪���ˡ��վ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Dz�خ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֪����"֮�꣬һ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ʢ�����ҡ� ����Ҳ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ˣ���Ϊ�й������̩�����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Ҫ�κ����ݴ��ˡ����Ӽ��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߾���ͬһ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dz��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خ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壬Ҳ������22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꡷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ź���Ҳû��ͻ�ƵĿ��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ʿһֱ�羪��֮��ʹ��خϣ��Ů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ѧ�Һ�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خ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DZ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صı��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ĥ�����ֹ��ֵ�Ӱ�ӣ���ǽ�ڵ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ܺ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š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꡷��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خ��Ϊ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ģ���ʵ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ϲ��дʫ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Ȼ��д��ʫ����ʫ���Ǵ����벻�����ľ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һ��ë��ϯ��ʫ�ʣ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졭��"һ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"�ġ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ڳ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ַ��ϣ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ʫ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15��ʱ��ͥ�����ش��ʣ�"�ĸ�"ʹ������ȫ�ҵ�����Ԩ������ס�İ˼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Ҳ���Ǹ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ͩ����"��ʼ�˷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"���Ĵ�ҹ���"��ĸ����Ӱ�첢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ʫ����ĸ�׳�¼��С�����ϣ�ֱ�����뿪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ĸ��ȥ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30���ʱ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Ů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17��ʱ����С�û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㵽���ַ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˱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̲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ʱ�����黹ͦ��죬��Ϊ�Ͼ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"�ڰ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ɻ���Ļ��в����ͽ̵�С��å����˵��ʱ����åҲ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Ĵ��е���ڡ���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С˵�г���ʹ�õķ�Χ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ͥ����ίҲ�Ǹ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dz���ݲ�خ����Ϊ��خ���ѵõĹ�������ð�ŷ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㡢��Ұ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ȴֻ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ȥڹ�͵�ʱ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Ȼ�Ⱥ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ض��ʣ���ǡǡ�⼸��ʹ����Զ��֪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70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Щ֪������һͬ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ֱ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خ�ı��Ӱ�籾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õ��£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خ�ĸ�Ů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뽻������خ����Ů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ı�ú���Ч�ʣ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Ҳ�ܹ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"��"��ѱ�罱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خ����Ʒ��һ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ø����ʽ�ıࡶԭҰ�����Դ˲�خ�Ǻܵ��ĵ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꡷��α��ı�ΪӰ����Ʒ��ȴԶû�д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Ļ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д�ú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ʾ�˵��"�ҵ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ˡ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ݳ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ɭ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ݣ���Ӧ����ϯ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00�������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ﰺ÷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"�й��˵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볡ȯ�ۼ۸ߴ�129��Ԫһ�ţ���ʮһ���ݳ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γ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"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ġ�"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Ը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ϲ��д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ƪС˵���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ɱ�ˡ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Ĺ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ʵ�ʣ����е�дС˵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硣��֪��д���Ӿ�Ҫռȥ������ʱ�䣬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ʹдС˵�ĸо�����Ӱ�졣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У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Ǵ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ú��ݡ���һ�괺���й���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ǧԪ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ಡ�IJ�خ�Ź��ò����DZ���ֻ�Ǻ������Ű�Ȩ����ʵ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Ȩ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ٺ����˸ıࡶ���꡷�İ�Ȩ����ʹ�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Ը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㣬Ҫû�к��֮�ǵ�дС˵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д�˼�ʮ�����Ӿ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û����ǵ��ݵ��¡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ġ�ţ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±��ɷ���ţ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̾�����Į�Ļ������ϣ�һ����ͨ��Ů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̲��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5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2��Ķ�����ڲɷ��У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ǰ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˹ǰ��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һ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ֻ�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һͬ������ɷ�һֱ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ʹ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춯�ص��¡���д�籾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dzɣ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ǿ�ң��йز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д�úܺÿ���ţ���ٳ���Ӣ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ʺ�����ȴ��֪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Ҹ��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Ͳ�خ���Ǹ�Ů��Ҳ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Ϸ��ң��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ӵķ�ʽҲ�Ƕ��صġ�Сʱ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ȥ��Ӿ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ˮ���ץס�ر߲����֣���خȴ��ס����ͷ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ޣ���خȴ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г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ٵIJ�خ���ų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ˤ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ˤ�ˣ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£���λ��ʦҲ�Ľ���Ϸ��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թ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飺"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خ��"��خ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ǿ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ɡ����ֿ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⸸�ף��Դ�ĸ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ܸм����ļ�ĸ����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еؽ������衣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ײˡ������Ϻ�һ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ܺõĺ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ʼ��û�л��ᡣ��خ��Ů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ر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һ�α仯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ǻ��Կɰ���С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Ƕ���ġ���خ�����д�£�"���и����ӣ�Ҳ��ԲͷԲ�ԣ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ǻ����˲��پ�����ʱ�䣬Ҳ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ʹ�ࡣ�Ҳ���̸���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¡�" ������خ�����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ס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˼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д����"��ע���Űְ֣�ͬʱ�����ܸе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˿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£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ǣ��ںܶ�ʱ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ʹ�࣬�����ܶ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ȥ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خֻ��ͨ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ʲôѽ��"��خ�ļ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ҩ�Ļ�ʿ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"�ϵ۰��ŵ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С��Ҳ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ô�ɰ������˾Ͳ�ͬ�ˣ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ɰ��ı��ݣ��ϵ۰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"��ο���ף�"��Ҳ�ɰ�ѽ��"��خ���ε�ЦЦ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û�а취��" �����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ʮ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г�Ϊ"�й���ɯʿ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ʧȥ������Ĺ�ʡ��Ȼ���Dz�خһ���˶��е�����é�ܡ��ͽ����ᡢ����Ķ���ͬ�̶ȵؾ����ˣ���һֱ���21���͵IJ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У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ʹ�࣬��Ҫд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Ҳ��ɣ���Խ���ж�˹̩Խ���ܡ�"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Ωһ�������ߵĶ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خ�ڲ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ţ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ηſ��˱���Ů��һ�Σ�"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 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һ����衷���dz�ϣ����خд�㶫������ʱ�IJ�خ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һ���ֶ��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д����"���ҵ�Ů������DZȽ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д�Ķ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С˵��ɱ�ˡ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Ƚ�רע�Լ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ܹ�д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ͱ����ˡ�"
��خ��Ů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ްθߡ�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λΪ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¿������屦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̳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ļ��죬�����ڳ�˯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һ����
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