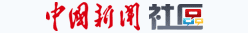°°°°”Ň—Ň”Ž∑ŇňŃ
°°°°ŌŽīĶ≥§Ķ—Ķń–°ňĶľ“
°°°°2005ńÍĶńīļŐž£¨ļÕ–°ňĶľ“Õűł’”–Ļż“ĽīőľŻ√ś£¨ «‘ŕňŻ–Żőš√ŇĶńľ“÷–°£ňŻń√≥Ų“Ľį—“Ý…ę°Ę∑ļ◊ҔҗҰʳŖĻů…ę‘ůĶń≥§Ķ—∂‘ő“ňĶ£ļÕ–Ňů”—ī”ĻķÕ‚¬ÚĶń°£ő“Ō÷‘ŕĽ÷łīīĶ≥§Ķ—Ńň°£Ō»īĶ“Ľ∂őń™‘ķŐōį…°£
°°°°’‚ «°∂”ĘłŮѶ Ņ°∑≥ŲįśļůĶńĶŕ∂ĢńÍ£¨°∂”ĘłŮѶ Ņ°∑ňý“ż∆ūĶń÷Ó∂ŗ∑īŌž£¨ĽĻĽō–ż‘ŕňŻ÷‹őߣ¨ĶęňŻŌŽĶń «īĶ≥§Ķ—°£į—ő“√«ĶĪ ĪĶńő īūĽĻ‘≠£¨īůłŇ «’‚—ýĶń£ļő™ ≤√ī–ī–°ňĶ£Ņő™ ĶŌ÷őń—ß√ő°£ ĶŌ÷Ńňőń—ß√őł… ≤√ī£Ņ‘ŕľ“īĶ≥§Ķ—°£
°°°°’‚÷ģļůő“√«√Ľ‘ŔŃ™ŌĶ£¨ňńńÍļů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(…Ō)√ś ņ£¨ń÷Ńň“Ľ≥°°į“ĽŇģŃĹľř°ĪĶńįś»®∑Á≤®£¨”÷ŃĹńÍ£¨Ō¬≤Ņ√ś ņ£¨◊‹Ļ≤ľ”∆ūņī75ÕÚ◊÷°£ő“Ņ™ ľ◊Ų◊‘ľļĶńŇ–∂Ō£¨ňŻīůłŇ≤Ę√Ľ”–Ľ÷łīīĶ≥§Ķ—£¨“Úő™ňŻĽĻŌŽ◊Ň–ī–°ňĶ£¨≥§Ķ—∂‘ňŻ£¨÷Ľ «łŲ”ņĺ√ĶńńÓŌŽ°£
°°°°“Űņ÷∆š Ķ“—¬Ů‘ŕňŻĶńőń◊÷ņÔ°£°∂”ĘłŮѶ Ņ°∑ņÔĺÕ”–£¨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ņÔ“≤”–°£÷Ľ «£¨ń«÷÷≤™ņ≠ń∑ňĻ ĹĶń”Ň—Ň°Ę śĽļĶń«ķ Ĺ£¨”√”ŕ°∂”ĘłŮѶ Ņ°∑ĶńĽ≥ĺ…∑«≥£«°«–£¨”√ĶĹ÷š”ÔņÔ£¨Ī„”––©≥Īļűļű°£“™÷™Ķņ£¨ňŻĶń∑‚√ś—Ł∑‚÷ųŐ‚ī «£ļ∂Ń–¬°∂◊”“Ļ°∑£¨ŅřĶĪīķ◊ Īĺľ“Ķń‘≠◊Ô”ŽņŪŌŽ°£
°°°°“ĽĪ唶ł√‘ŕ’‚łŲ Īīķ≥ŲŌ÷Ķń–°ňĶ£¨“Úő™–īĶń «ĶĪīķ∑ŅĶō≤ķ…Ő»ň°£∑ŅĶō≤ķ’‚łŲī Ľ„£¨őř–őľšĺū◊°Ńňļ‹∂ŗ»ňĶń√őŌŽ°£∂Ý≥Ň∆ūĽÚīÚňť’‚√őŌŽĶńĶō≤ķ…Ő√«£¨ļ‹ń—»√ő“√«”√ĺī—Ų”Ž»»įģ»•–ő»›°£Ķęő“√«ņŽ≤ĽŅ™ňŻ√«£¨“≤Ķń»∑ļ‹ŌŽŃňĹ‚£¨ňŻ√«ő™ ≤√īŅ…“‘∑≠‘∆ł≤”ÍĶō◊ů”“ő“√«Ķń–“ł£°£
°°°°ī”°∂”ĘłŮѶ Ņ°∑Ņ™ ľ‘ń∂ŃÕűł’£¨ļ‹ń—ŌŽŌůňŻ≥żŃň”Ň—Ň£¨ĽĻ”–≤–ŅŠ°Ę∑ŇňŃĶń“Ľ√ś£¨ «‘ŕ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Ķń–ū Ų÷–°£Ķę «į—ňŻłŁ‘ÁĶń◊ų∆∑°∂‘¬ŃŃĪ≥√ś°∑∑Ň“Ľ∆ū∂Ń£¨”÷ň∆ļűń‹ł–ĶĹń≥÷÷≥–Ĺ”°£ń« «∑Ž–°ł’ŇńŃňĶÁ ”ĺÁ”÷ĪĽłť«≥Ķń◊ų∆∑£¨Õ¨—ý «∑ŇňŃ°Ę≤–ŅŠ”Ž”Ň—ŇĶńľĮļŌŐŚ°£’‚—ýŅīņī£¨°∂”ĘłŮѶ Ņ°∑łŁŌŮ“ĽłŲ◊ų∆∑ĶńņżÕ‚°£
°°°°Ī»∆ū∆šňŻ◊ųľ“£¨Õűł’Ķńĺ≠ņķŌŗ∂‘łī‘”£¨ňŻ…ķ”ŕ–¬Ĺģ£¨…ŔńÍ ĪīĶĻż≥§Ķ—£¨«ŗńÍ Īī”–¬ĹģĶĹĪĪĺ©◊∑—įőń—ß«ŗńÍ√ő£¨”ŽňŻļŌ◊ų∂ŗńÍĶń‘ūĪŗ÷‹≤ż“Ś≥∆ňŻő™÷–ĻķĶńņ≠ňĻĶŔńý°£ĶęňŻļ‹Ņž”÷◊™…ŪŌ¬ļ££¨ű“…Ū”ŕ…ŐĹÁ≤Ę◊™’Ĺ”ŕļ£ńŌ£¨“≤“ÚīňńŅ∂√Ńňļ‹∂ŗ…ŐĹÁ»ňőÔĶńł°≥Ń°£÷ŃĹŮ£¨ňŻĽĻļÕ“Ľ–©»ňĪ£≥÷◊ŇŃ™ŌĶ£¨≤Ęł–Ņģ◊ŇňŻ√«Ķń√Ł‘ň°£∂Ý’‚–©£¨ĻĻ≥…ŃňňŻ–ī’‚“ĽŌĶŃ–◊ų∆∑Ķń…ķĽÓ◊ ‘ī°£
°°°°∂Ń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£¨ń‹ŅīĶĹ“Ľ∂‘ň∆ŃĶ»ň”÷ŌŮīÓĶĶĶńń–Ňģ°™°™∑Ž Į”ŽĹ™«ŗ°™°™”Ň—Ň∂Ý≤–ŅŠĶń”ŻÕŻőŤĶł£¨ňŁ Ī∂ÝĪĽĹ‚∂Ń≥…“į–ń£¨ Ī∂ÝĪĽ∂‘”¶≥…÷–Ļķ√ő°£ĶĹĶ◊ ≤√ī «÷–Ļķ√ő£¨ĽÚ’ŖňŁ÷Ľ «’‚łŲ Īīķ”ŻÕŻ”Ž«ťł–’ű‘ķļÕ≤©řńĶńīķ√Żī £ŅňŁŃÓ»ňŃ™ŌŽĶĹŃň°∂‘¬ŃŃĪ≥√ś°∑÷–Ķńń≤ńŠ”ŽņÓ√Á°£∂‘£¨ňŻ√«“—ĺ≠ «Õűł’’‚ņŗ–°ňĶ÷–ĪÍ«© ĹĶń»ňőÔ◊ťļŌ°£“Ľ÷÷‘ŕĪū»ňĪ Ō¬Ņ…≥∆÷ģįģ«ťĶń∂ęőų£¨‘ŕÕűł’Ī Ō¬£¨◊‹”–ňŁ—™Ń‹Ń‹Ķń“Ľ√ś£¨≤ĽĻżňļŅ™ĶńÕ¨ Ī£¨Õűł’”÷◊‹»√ń„ŌŽĶĹ“Ľ÷Ľ ‹…ňĶńņŌĽĘ£¨‘ŕŐÚů¬◊‘ľļĶń…ňŅŕ°£
°°°°…ķĽÓ÷–ĶńÕűł’Ō≤Ľ∂√ŻŇ∆£¨ļ»—ůĺ∆£¨ļ‹∂ģĶ√ŌŪ ‹Ķę”÷ļ‹»›“◊≥ŲņŽ∑ŖŇ≠°£ňŻĽŠ“ĽłŲ»ň»•“Űņ÷ŐŁŐżĻŇĶš“Űņ÷£¨ŐżĶ√őřŌř…ňĽ≥ Ī◊‹ «ŌŽő™ ≤√ī≤Ľ»•īĶ≥§Ķ—°£ňŻ∂‘◊‘ľļ◊ų∆∑Ķń∆ņľŘ◊‹ «ŃĹľę£¨“ĽĽŠ∂ý◊‘»ŌŇ£Ķ√≤Ľ––£¨“ĽĽŠ∂ý”÷ĺűĶ√√Ľ“‚“Ś°£ń«≥°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įś»®∑Á≤®£¨‘ŕĪū»ňŅīņīļůĻŻļ‹—Ō÷ō£¨ňŻĶń◊ňŐ¨‘Ú «£ļňśňŁ»•°£ Ļń„őř∑®į—ő’£¨ňŻĶĹĶ◊ńńłý…Ůĺ≠◊Óīŗ»ű°£
°°°°“Úő™°∂”ĘłŮѶ Ņ°∑‘ŕĻķÕ‚Ķń≥Ųįś”Ž”įŌž£¨īň ĪĶńÕűł’’ż ‹—Ż≤őľ”“ĽłŲҶ‘ľĶń◊ųľ“īŚĽÓ∂Į£¨Ň¶‘ľ“≤ «īļŐž£¨ňý“‘ňŻ‘ŕ” ľĢņÔňĶ£ļńŕ–ńņÔ”–ļ‹∂ŗ—’…ę°£∂Ý‘ŕő“Ņīņī£¨Õűł’ĺÕ «“ĽłŲ”–ļ‹∂ŗ—’…ęĶń◊ųľ“£¨ňŻį—’‚–©£¨∂ľļŃ≤ĽĹŕ÷∆Ķō»ųłÝŃňňŻĶń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°£
°°°°1
°°°°ő :‘ŕ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Ķń’żőń ◊“≥£¨ń„÷£÷ōĶō∑ŇŃňĶ¬Ļķ◊ųľ“¬Ū∂°°§ÕŖ∂Ż‘ůĶń“Ľ∂őĽį£ļ°įő“÷™Ķņő“≤Ľ «÷™ ∂∑÷◊”£¨ő“ļ‹«Ś≥Ģ°≠°≠ő“√«÷™ĶņĶ√Őę∂ŗŃň£¨ő“√«Ķń÷™ ∂≥…ő™Ńňő“√«Ķń“Ľ÷÷įŁł§°£°Ī“Ľį„ņīňĶ£¨◊ųľ“į—“Ľ∂őĪū»ňĶńĽį∑Ň‘ŕ–°ňĶ«į√ś£¨ «”–”√“‚Ķń°£ń„Ķń”√“‚ «‘ŕ ≤√īĶō∑Ĺ£ŅĽÚ’ŖňĶ£¨ń„”√ňŁņīŐŠ–—ń„ ≤√ī£Ņ
°°°°īū£ļ÷–Ļķ◊ųľ“Ō≤Ľ∂√į≥š÷™ ∂∑÷◊”£¨ĽÚ’Ŗ—ß’Ŗ£¨ňŻ√«“‘ő™◊‘ľļļ‹”–÷™ ∂£¨“‘ő™◊‘ľļ’śĶńŅ…“‘≥…ő™ń«÷÷ľ»ł…弔÷ŐŚ√śĶń»ň£¨ő™Ńň—ŕ ő◊‘ľļĶńŃťĽÍ£¨ĺÕŌŽ”√°į÷™ ∂°Ī»•≤Ļ≥š£¨∆š Ķ£¨ňŻ√«īŪŃň£¨◊ųľ“◊‹ ««ßīĮįŔŅ◊£¨√¨∂‹÷ō÷ō£¨‘ŕĶņĶ¬ļÕ»ňłŮ…Ō”–ļ‹∂ŗ»űĶ„£¨Ņ…ĺÕ «’‚—ýĶń»ň£¨“ĽīķīķĶō–ī≥ŲŃň»ňņŗ◊ÓőįīůĶń◊ų∆∑°£“Úő™ňŻ√«ňĶŃň’śĽį£¨ĪŪīÔŃňŐŚ—ť£¨∂ĮŃňł–«ť°£
°°°°‘ŕ’‚Īĺ ť÷–£¨ń„Ņī≤ĽĶĹ°∂”ĘłŮѶ Ņ°∑÷–”Ę”ÔņŌ ¶ń«—ýŃÓ»ňŃĮŌß∂Ý”÷–ń…ķ◊ūĺīĶń»ň£¨“≤ŐŚĽŠ≤ĽĶĹ ≤√īĹ–» ī»”ŽłŖĻů£¨√ŅłŲ»ň∂ľļ›īŰīŰĶō◊∑÷ū”ŻÕŻ£¨»√ń„ļ‹ń—”√«ťł–»•»ę–ń”ĶĪߣ¨Ķęń„Īō–Ž’ż ”£¨“Úő™ňŁįŁļ¨◊Ň’‚łŲ ĪīķĶń√¨∂‹”Ž√ō√‹°£
°°°°2
°°°°ő £ļňš»Ľļ‹Ō≤Ľ∂ń„Ķń°∂”ĘłŮѶ Ņ°∑£¨Ķęī”īī◊ųņīŅī,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łŁŅ…Ĺ”–Ýń„Ķń°∂‘¬ŃŃĪ≥√ś°∑£¨“Úő™ňŁ“≤‘ŕ ‘Õľő™’‚łŲ Īīķ◊Ółī‘”Ķń“Ľ»ļ»ňĶńĺę…ŮĽ≠ŌŮ°£ń„”–∂ŗńÍī”…ŐĶńĺ≠ņķ£¨”»∆šĺ≠ņķĻż…Ō ņľÕĺŇ ģńÍīķļ£ńŌ∑ŅĶō≤ķĶńłŖ≥Ī”ŽĶÕĻ»£¨’‚ «ń„≤Ľ∂Ōīī◊ų≥Ų’‚ņŗŐ‚≤ń◊ų∆∑Ķń‘ī»™”Ž∂ĮѶ°£Ķę «£¨ő“√«“≤÷™Ķņ£¨“™ ť–ī◊‘ľļ žŌ§ĽÚ’Ŗ‘Ýĺ≠ žŌ§Ķń“Ľ»ļ»ň£¨“≤Ņ…ń‹ĽŠ”–◊‘ő“’Ōį≠£¨őř∑®«Ó–őĺ°Ōŗ°£ń„–ī◊ų’‚ņŗŐ‚≤ńĶń ĪļÚ”–¬ū£Ņ
°°°°īū£ļ∆š Ķ£¨őř¬Řńń“Ľ≤Ņ◊ų∆∑£¨»ę «–ī◊‘ľļ°£∂ľ «∑«≥£łŲ»ňĽĮĶń£¨ő“Ķń◊ų∆∑£¨Īū»ň“ĽŅī£¨ĺÕ÷™Ķņ”–◊Ň«ŅŃ“ĶńÕűł’ļŘľ£°£ĶĪ»Ľ£¨∑Ž Į≤Ľń‹łķÕűł’Ľ≠Ķ»ļŇ£¨Ķę «£¨“ĽłŲ◊ųľ“£¨ňŻĽŠį—◊‘ľļĶń»ę≤ŅĹĢ»ůĹÝňŻĶń÷ų»ňĻę…Ū…Ō°£ī”’‚łŲ“‚“Ś…ŌňĶ£¨–°ňĶľ“”–≥ŠįÚ£¨ń‹∑…∆ūņī£¨ŅÁĻż–Ū∂ŗĪūĶń––ĶĪňýőř∑®‘ĹĻżĶńĹÁŌŖ°£∂Ý«“£¨”ŽĪūĶń÷–Ļķ◊ųľ“Ī»£¨ő“ļ√ŌŮŐōĪū√Ľ”–’Ōį≠£¨◊‹ «ŌŽ«Óĺ°◊‘ľļ£¨÷Ń”ŕ’‚łŲ–őŌůĹŮļů‘ŕőń—ß ∑…Ō£¨Īū»ň‘ű√īňĶ£¨ń«ňśĪ„į…°£
°°°°3
°°°°ő :ń„Ķń‘ūĪŗ÷‹≤ż“Ś‘ŕ«į—‘÷–ňĶ°∂”ĘłŮѶ Ņ°∑ļů£¨ń„īÚň„–ī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£¨Ķę≥Ŕ≥Ŕ≤ĽŅ™Ī °£ń„ňĶń„‘ŕ—į’“”Ô—‘ļÕ–ū Ų∑Ĺ ĹĶńő Ő‚°£ń«√ī‘ŕń„∂ĮĪ –ī◊ų÷ģļů£¨ń„»Ōő™◊‘ľļ’“ĶĹŃň Ű”ŕ◊‘ľļ’‚łŲŐ‚≤ńĶń”Ô—‘”Ž–ū Ų∑ŠŬū£Ņ’‚ «ń„∆ýĹŮő™÷Ļ◊Ó≥§Ķń“Ľ≤Ņ–°ňĶ£¨…ŌŌ¬ĺŪŃĹ≤Ņ°£ī¶ņŪ’‚√ī≥§∆™∑ýĶń–°ňĶ£¨ŅŌ∂®ļÕ“Ľ∂Ģ ģÕÚ◊÷Ķń≤ĽÕ¨°£ń„ő™ňŁ◊ŲŃň‘ű—ýĶń◊ľĪł°£ń„ňĶń„”√ŃňőŚńÍ ĪľšÕÍ≥…ňŁ°£’‚őŚńÍń„ «‘ű—ý∂»ĻżĶń£¨ «◊®–ń÷¬÷ĺĶō–īňŁńō£ŅĽĻ «–ī“Ľ–ī°ĘÕ£“ĽÕ££¨◊Ų–©ĪūĶń ¬°£ļ√»√ňŁ‘ŕ“Ľ∂® Īľš∑Ň“Ľ∑Ň£¨◊Ų–©Ķų’Ż°£ŐżňĶń„‘ŕ’‚őŚńÍ÷–ĽĻ≤ŰŃň“Ľ–©”Žń„őřĻōĶń ¬£¨“Úő™∑ŖŇ≠∂Ý»•ő™Īū»ňīÚĪß≤Ľ∆Ĺ°£’‚ĽŠ”įŌžĶĹń„Ķń–ī◊ų¬ū£ŅĽĻ «ĽŠ»√ń„∂‘ňý–īĶń∂ęőų”Žňý–īĶń Īīķ”–łŁ«Ś–—ĶńņŪĹ‚°£
°°°°īū£ļŅ™ ľő“ŌŽ–ī≥Ų“Ľ≤Ņĺę÷¬Ķń–°ňĶ£¨Ņ… «£¨ĪŪīÔ≤Ľ≥©£¨»Ľļů£¨ő“Ņ™ ľĪšĶ√∑ŇňŃ∆ūņī£¨ĺĻ»ĽÕŰ—ůŪßňŃŃň£¨75ÕÚ◊÷Ķń–°ňĶ»√ő“ī”Ņ™ ľĶńňś–ńňý”Ż£¨–ī–īÕ£Õ££¨ĶĹ◊ÓļůŅ™ ľĹÝ»ŽŃň√ŅŐž–ī◊ų≤Ľ÷ĻĶń◊īŐ¨°£÷Ľ «ő“ĽŠ‘ŕ–ī◊ų÷–ĽĽĶō∑Ĺ£¨ī”ļ£ńŌĶĹőŕ¬≥ńĺ∆ŽĶĹĪĪĺ©£¨ĶĹĪĪīųļ”°≠°≠∆šľš£¨≤Ľ∂Ō”––¬∑Ę…ķĶń ¬«ť”įŌžłńĪšő“Ķń‘≠…Ťľ∆°£ő“Ļż”ŕĻō◊ĘŌ÷ Ķ£¨ňý“‘ő“√ś∂‘Ō÷ ĶŐōĪūŅ ÕŻ∑Ę—‘£¨’‚÷÷«ť◊īŅŌ∂®ĽŠĹÝ»Žő“Ķń–°ňĶ÷–°£»√∑Ž ĮļÕĹ™«ŗĹ•Ĺ•ĽÓ∆ūņī£¨≤Ę»√»ňń‹»Ō≥ŲňŻ√«ĺŅĺĻ «ň≠°£
°°°°4
°°°°ő :–°ňĶĶńŅ™Õ∑ «1999ńÍ£¨–°ňĶĶńĹŠő≤“—ĺ≠ĶĹŃň2009ńÍ£¨“≤ĺÕ «ňĶ£¨ń„–ī÷–Ļķ∑ŅĶō≤ķ“Ķ ģńÍ£¨–īĶĹŃňņŽŌ÷ ĶĹŁĶ√≤Ľń‹‘ŔĹŁĶńńÍ∑›°£ĶĪĹŮ£¨√ŅłŲĻķ»ň∂‘∑ŅĶō≤ķ“Ķ∂ľ”–◊‘ľļĶńňĶī«£¨ĶęŌŽī”ń„Ķń–°ňĶ÷–ņī—į«ůĶĪīķ∑ŅĶō≤ķ“ĶĶńĹ‚Ő◊∑Ĺ Ĺ£¨”÷ «≤ĽŅ…ń‹Ķń°£“Úő™–°ňĶ≤Ľ≥–Ķ£’‚łŲ“ŚőŮ°£ő“łŲ»ň£¨ī”ń„–°ňĶĶńĹŠő≤£¨–ŠĶĹŃň∑Ž Į’‚“Ľīķ√Ů◊Ś∆ů“Ķľ“Ķńňř√Ł“‚ő∂°£ĶĪń„ňĶ°į∑Ž ĮĺűĶ√◊‘ľļ’‚“Ľ…ķ∂‘”ŕ–Ū∂ŗ ¬«ťĶńŇ–∂Ō£¨∆š Ķ∂ľīŪŃň°£°ĪĶń ĪļÚ£¨ń„Ī≥ļůĶń“‚ļ≠ « ≤√ī£Ņ
°°°°īū£ļő“Ņ™ ľ◊ųŃň∑ŁĪ £¨∑Ž Į»•ÕĶ«ť ĪŅīĶĹŃň√ŇŅŕ“Ľňę≥¨īůĶń–¨◊”£¨ňŻŌŽŌůňŻĶńĶ¬Ļķ«ťĶ–°™°™Ĺ™«ŗĶńÕ‚Ļķń–”—ŅŌ∂® ≤√ī∂ľ «īůĶń£¨◊‘ľļ ≤√ī∂ľ «–°Ķń£¨Ņ… «£¨‘ŕ–°ňĶĹŠ Ý Ī£¨ňŻ÷’”ྯĶĹŃň◊‘ľļĶń«ťĶ–ń«łŲĶ¬Ļķ»ňĺĻ»ĽĪ»◊‘ľļįę£¨”–Ņ…ń‹ ≤√ī∂ľĪ»◊‘ľļ–° Ī£¨ňŻ÷’”ŕŅ™ ľ≥ĻĶ◊Ľ≥“…◊‘ľļ°£ŌŮ∑Ž Į’‚—ý“Ľīķ√Ů◊Ś◊ Īĺľ“◊ŖŌÚĪĮĺÁ «Īō»ĽĶń£¨“Úő™ňŻ√«ĽÓ‘ŕ’‚łŲ Īīķ£¨≤ĽŅ…ń‹’ż»∑°£
°°5
°°°°ő :ő™ ≤√ī≤ĽŅ…ń‹’ż»∑£Ņ
°°°°īū£ļňŻ√«‘ŕ’ű«ģĶńĻż≥Ő÷–£¨…ŪļůŃŰŌ¬Ńň“ĽŐű≥§≥§Ķńő≤įÕ£¨ňŻ√«įŕÕ—≤ĽŃň’‚łŲ°£ňŻ√«‘ŕľ–∑ž÷–…ķīśľŤń—°£»ň√Ů≥ūļřňŻ√«£¨÷™ ∂∑÷◊”ļřňŻ√«£¨’Ģłģ≤Ľ¬ķ“‚ňŻ√«£¨ňŻ√«…ķĽÓĶ√ľę∆šŅ÷匰£∂Ý∑Ž Į◊ÓļůĶńĹŠĺ÷£¨ī”“ĽłŲ≥Á…– –≥°ĺ≠ľ√Ķń»ň£¨◊Ó÷’“ņłĹ”໮Ѷ£¨≥…ő™»®Ń¶◊ ĪĺĶńĪš÷÷£¨ «”–Ōů’ų“‚“ŚĶń°£
°°°°6
°°°°ő £ļ°∂‘¬ŃŃĪ≥√ś°∑÷–”–“Ľ∂‘ń≤ńŠ”ŽņÓ√Á°£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÷–£¨≥żŃňņŗň∆’‚∂‘ŃĶ»ňĶń∑Ž Į”ŽĹ™«ŗÕ‚£¨ĽĻ”–“ĽłŲ–÷Ķ‹į„Ķń»ňőÔĻō ų£¨ļÕ∑Ž ĮīÚ∆ī∂ŗńÍ£¨Ĺ™«ŗ≤ő”ŽĶĹ∆ů“Ķ÷–ņī£¨ĽĻ»√ňŻ√«Īňīňľš”–ŃňņŻļ¶≥ŚÕĽ°£ő“÷™Ķņń„ŐōĪūŌ≤Ľ∂°∂√ņĻķÕý ¬°∑’‚≤ŅĶÁ”į£¨–ī’‚»żłŲ»ňőÔĻōŌĶ Ī£¨ń„ĽŠ≤ĽĽŠŌ£ÕŻ»ň√«∂Ń≥Ųņŗň∆°∂√ņĻķÕý ¬°∑÷–ń«÷÷ł– ‹°£
°°°°īū£ļ°∂√ņĻķÕý ¬°∑∂‘ő“”įŌž∂ŗńÍ£¨ő“◊‹ «ĽŠ÷ō–¬ŅīňŁ°£ő“Ō≤Ľ∂”√ŃĹ»żłŲ»ň»•ĹŃ∂Į≥Ų“ĽłŲīůĶń ņĹÁ°£ő““≤Ō≤Ľ∂–īń–ŇģĻōŌĶĶńĻ ¬£¨»ÁĻŻ√Ľ”–’‚–©£¨’‚ ņĹÁŐęőř»§Ńň°£
°°°°7
°°°°ő £ļń„Ķń”Ô—‘“Ľ÷Ī”–÷÷“Űņ÷–‘°£∂Ý’‚“Űņ÷Ķńł–ĺű”÷īÝ◊Ň „«ť–‘£¨“≤Ņ…≥∆÷ģő™…ňł–į…°£’‚÷÷»Š»ŪĶńĶų◊”◊Ó ļŌĽ≥ĺ…£¨Ķę «”√ĶĹ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÷–£¨”––©∂Ń’ŖĽŠĺűĶ√≤ĽĻĽ°įļ›°Ī°£ňý“‘ī”‘ń∂Ńł–ĺűņīňĶ£¨’‚÷–ľšĶń«ťł–”––©≥Ī°£≤Ľ÷™ń„Õ¨≤ĽÕ¨“‚ő“Ķń’‚÷÷Ņī∑®£ŅňĶĶĹ’‚ņŗŐ‚≤ńĶń–ī◊ų£¨ő“◊‹ «ń‹ŌŽĶĹĶ§ńŠ∂Ż°§Ńű“◊ňĻ÷ų—›Ķń“Ľ≤ŅĶÁ”įĹ–°∂—™…ęļŕĹū°∑£¨ī¶ņŪĶń∑Ĺ Ĺ∑«≥£ľÚ弰Ę÷ĪĹ”£¨ľłļű÷ĽľŻ»ňőÔĶń∂Į◊ų”Ž––ő™£¨Ķę «ŅīĶ√»ňĺ™–ń∂Į∆«°£ő“łŲ»ňĺűĶ√£¨ń«≤ŇĹ–ļ›°£∂Ýń„Ļ«◊”ņÔ°≠°≠ň∆ļűļ›≤ĽŌ¬ņī°£Ķę”÷ļ‹ŌŽļ›īŰīŰ°£ő“‘Ýĺ≠ļ‹ŌŽ”√ŃĹłŲī ņī–ő»›ń„£ļ”Ň—Ň”Ž∑ŇňŃ°£Ō÷‘ŕĺűĶ√£¨”√’‚ŃĹłŲī –ő»›’‚Īĺ ť“≤Ņ…°£ĶęňŁőř“… «∑«≥£√¨∂‹Ķń“Ľ∂‘ī °£
°°°°īū£ļļ‹ļ√£¨ő“Ō≤Ľ∂£¨”Ň—Ň”Ž∑ŇňŃ°£ĶĪő“∑ĘŌ÷ő“Ĺ•Ĺ•į—◊‘ľļĶń”«…ň◊Ę»ŽĶĹ∑Ž Į…Ū…Ōļů£¨ő“Ņ™ ľ–ň∑‹Ńň£¨”–ł–ĺűŃň°£ĶĪő“∑ĘŌ÷∑Ž ĮĺĻ»ĽŌŮ∂Ū¬řňĻ»ňń«—ý£¨”–Ńň∑ŠłĽĶń«ťł– Ī£¨ő“ł–ĺűĶĹŐōĪū≥…Ļ¶°£
°°°°8
°°°°ő :“Úő™°∂”ĘłŮѶ Ņ°∑£¨ń„ĽŮŃňļ‹∂ŗĹĪ£¨≤Ę«“◊ų∆∑ĪĽ“ŽĶĹĻķÕ‚°£“Úő™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£¨ń„“≤Ķ√ĶĹ“Ľ–©Õ‚Ļķīę√ĹĶńŅ’«įĻō◊Ę°£Ķęő“ł–ĶĹŃĹ’ŖĶńĻō◊ĘĹĻĶ„≤Ľ“Ľ—ý°£«į’ŖĶńĻō◊ĘłŁīÝ”–őń—ß”ŽłŲ»ňľ«“šĶńĻ≤√ý°£ļů’Ŗ‘Ú «“Úő™ń„ňý…śľįĶńŐ‚≤ń”ŽŌ÷ Ķő Ő‚°£ő“łŲ»ňŌ≤Ľ∂°∂”ĘłŮѶ Ņ°∑łŁīů”ŕ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°£’‚ «“ĽłŲ«ťł–Ķń∆ņŇ–£¨∂Ý≤Ľ «◊ų∆∑ļ√ĽĶĶń∆ņŇ–°£»ÁĻŻļ‹∂ŗ»ň∂ľŌŮő“’‚—ý£¨ń„őīņīĶńīī◊ųĽŠ≤ĽĽŠ ‹”įŌž£Ņ
°°°°īū£ļő“Ķń–ī◊ų◊‹ «ŃĹĻ…°£“Ľ÷÷ «°∂”ĘłŮѶ Ņ°∑£¨“Ľ÷÷ «°∂ł£≤ľňĻ÷š”Ô°∑°£ő“ĽŠįī’’◊‘ľļĶńł–ĺű»•–īŌ¬“Ľ≤Ņ–°ňĶ°£Ī»»Áő“Ō÷‘ŕ‘ŕ√ņĻķŅ™ ľ–īĶń–°ňĶ°∂ĻōĻōŲ¬ūĮ°∑ĺÕ◊Ŗ‘ŕ°∂”ĘłŮѶ Ņ°∑ń«Ļ…Ķņ…Ō°£ő“ļ‹łŖ–ňń„√«Ō≤Ľ∂°∂”ĘłŮѶ Ņ°∑£¨ļ√į…£¨ĽĻĽŠ”–Ķń°£
°°°°9
°°°°ő :ń„Ō÷‘ŕ‘ŕҶ‘ľ≤őľ”“ĽłŲĹ–ART OMI LEDIG HOUSEĶń◊ųľ“īŚĽÓ∂Į£¨ŐłŐłń„‘ŕҶ‘ľĶń«ťŅŲ°£Õ‚√ś ņĹÁ»√ń„∂‘◊‘ľļĶńīī◊ų”– ≤√īłŁ–¬ĶńņŪĹ‚£Ņ
°°°°īū£ļҶ‘ľ√Ľ”–»√ő“’ūĺ™£¨÷Ľ «ĺűĶ√ļ√°£ő“◊°‘ŕ55Ĺ÷£¨◊ŖĶĹįŔņŌĽ„ĺÕőŚ∑÷÷”£¨ő“ŅīŃň°∂łŤĺÁ”ńŃť°∑£¨ń«Őž‘ŕĶĻ Ī≤Ó£¨ňý“‘ņŌ «ņߣ¨Ķę «£¨ń«łŲ≥™”ńŃťĶńń–—›‘Ī’ś «Őę∂Į«ťŃň£¨ňŻ“ĽīőīőĶō”√ žŌ§Ķń“Űņ÷į—ő“≥≥–—°£÷ĪĶĹő“≤ĽņßŃň£¨Ņ™ ľń¨ń¨Ķō°Ę…Ó«ťĶō–ņ…Õ◊ŇňŻ°£‘ŕŃ÷ŅŌ÷––ńŅīń™ňų∂ŻňĻĽýĶńłŤĺÁ Ī£¨ő“≤Ň’ś’żĶōĪĽ’ūĺ™£ļ…ŪĪŖňý”–ń«–©ń–ń–ŇģŇģ£¨ņŌņŌ…Ŕ…ŔĺĻ»Ľłķő““Ľ—ý žŌ§’‚≤Ņ∂Ū¬řňĻ»ňĶńłŤĺÁ£°ń„ňĶҶ‘ľ»ň”–√Ľ”–őńĽĮ£Ņő“Ņ™ ľĽ≥“…ń«–©‘ŕҶ‘ľ”ŽĪĪĺ©÷ģľšņīĽōŇ‹ĶńőńĽĮřÁŅÕ√«£¨ňŻ√«√Ľ”–őńĽĮ°£ń„Ņ…“‘ŐžŐž‘ŕĶÁ ”…ŌŅīĶĹňŻ√«£¨ňŻ√«ŐōĪūŌ≤Ľ∂ĪŪ√śĶń°į–¬Ō °Ī∂ęőų£¨≤Ę√Ľ”–ŌÚ ņĹÁ…ÓŅŐ°Ę…Ó«ťĶōĪŪīÔňŻ√«◊‘ľļĶńĻķľ“°£ő“łŁľ”ľŠ∂®Ńň£¨”√≥§∆™–°ňĶĶń∑Ĺ Ĺ£¨»•–ī◊‘ľļ žŌ§Ķń…ķĽÓ£¨»Ľļů£¨»√Ҷ‘ľ“‘ľį»ę ņĹÁŅīĶĹő“Ķń–°ňĶ°£
°°°°ňÔ–°ń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