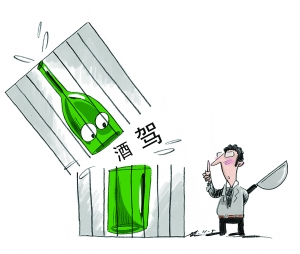°°°°∑®¬…ń‹≤Ľń‹“ĽĶ∂«–£Ņ
°°°°ĹŁ»’£¨◊ÓłŖ∑®‘ļłĪ‘ļ≥§’ŇĺŁĪŪŐ¨°į◊Ūľ›≤Ę∑«“Ľ¬…»Ž–Ő°Ī£¨łýĺ›–Ő∑®◊‹‘ÚĶŕ13ŐűĻś∂®£¨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ő£ļ¶≤ĽīůĶń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°£’‚łŲňĶ∑®“ż∑ĘŃňĺřīů’ý“ť°£įī’’∆’Õ®»ňĶńņŪĹ‚£¨÷Ľ“™ Ķ ©Ńň–Ő∑®Ļś∂®Ķń––ő™£¨őř¬Ř«ťĹŕ«Š÷ō”Ž∑ŮĺýĻĻ≥…∑ł◊Ô£¨√Ľ”–ņżÕ‚£¨’‚÷÷“ĽĶ∂«–Ķń◊Ų∑®ŐŚŌ÷Ńň∑®¬…Ķńł’–‘°£Ō÷‘ŕ≤ŇŐżňĶĽĻ”–Őű°į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°Ęő£ļ¶≤Ľīů£¨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°ĪĶń∑®¬…£¨»√»ň≤ĽĹ‚∆š“‚°£
°°°° Ķľ …Ō£¨‘ŕő“Ļķňĺ∑® Ķľý÷–£¨°įŌ‘÷Ý«ŠőĘ≤Ľ «∑ł◊Ô°Ī“—ĪĽĻ„∑ļ ”√£¨Ī»»Á»ň√«∂ľ÷™Ķņ£¨Ļ “‚…ňļ¶ňŻ»ň…ŪŐŚ÷¬»ň«Š…ňĶń£¨ĺÕĻĻ≥…Ļ “‚…ňļ¶◊Ô£¨“™◊∑ĺŅ–Ő ¬‘ū»ő°£Ņ… «£¨‘ŕĻęį≤≤Ņ2005ńÍ≥ŲŐ®Ķń°∂Ļęį≤ĽķĻōįžņŪ…ňļ¶įłľĢĻś∂®°∑Ķŕ∂Ģ ģĺŇŐű÷–Ļś∂®£¨∂‘Ļ “‚…ňļ¶ňŻ»ň÷¬«Š…ň£¨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°Ęő£ļ¶≤Ľīů£¨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Ķń£¨”¶ĶĪ“ņ∑®”Ť“‘÷őį≤Ļ‹ņŪī¶∑£°£īňÕ‚£¨∂‘”ŕĻ “‚…Ī»ň’‚—ýĶń÷ō◊Ô£¨“≤≥ŲŌ÷Ļż ”√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≤ĽĻĻ≥…∑ł◊ÔĶńŇ–ņż°£
°°°°»ň√«≤Ľ√ųį◊£¨ľ»»Ľ«Š…ň“—ĺ≠īÔĶĹĻ “‚…ňļ¶∑ł◊ÔĶńĪÍ◊ľ£¨ő™ ≤√īĽĻĽŠ”–“—ĺ≠īÚ≥…«Š…ň£¨”÷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Ķń«ť–ő£¨∂Ý«“√ų√ų∂ľĻ “‚į—»ňīÚ≥…«Š…ňŃň£¨‘ű√īĽĻĽŠ°į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°Ęő£ļ¶≤Ľīů°Īńō£Ņ
°°°°’‚Őű°įŌ‘÷Ý«ŠőĘ≤Ľ «∑ł◊Ô°ĪĶń∑®¬…£¨ ĻĶ√“Ľį„ő•∑®”Ž–Ő ¬ő•∑®‘≠Īĺ√ų»∑Ķń“ĽĶ∂«–ĹÁŌř£¨ĪšĶ√≤Ľń«√ī»∑∂®Ńň°£ń«√ī£¨–Ő∑®ő™ ≤√ī“™’‚—ýĻś∂®£Ņ
°°°°Ļę√ŮőĪ‘ž…Ū∑›÷§ĪĽ–Żłśőř◊Ô
°°°°‘ŕ…Ōļ££¨‘Ý∑Ę…ķĻż“Ľ∆ūĻ “‚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£¨”÷ĪĽ–Żłśőř◊ÔĶńįłņż°£ĪĽłś»ň’Ň√ņĽ™≤Ľ…ų“Ň ß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£¨“Ú∆šĽßŅŕőī¬š Ķ£¨őř∑®ŌÚĻęį≤ĽķĻō…Í«Ž≤Ļį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£¨ňž”ŕ2002ńÍ5‘¬Ķ◊£¨“‘∆šĪĺ»ň’’∆¨ļÕ’ś ĶĶń–’√Ż°Ę…Ū∑›÷§ļҬŽļÕ‘›◊°ĶōĶō÷∑£¨≥Ų◊ »√ňŻ»ňőĪ‘žŃň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1’Ň°£ļůĪĽ“‘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◊ÔŐŠ∆ūĻęňŖ°£
°°°°…Ōļ£ –ĺ≤į≤«Ý∑®‘ļĺ≠…ůņŪ»Ōő™£¨’Ň√ņĽ™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Ķń––ő™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£¨ő£ļ¶≤Ľīů£¨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°£ĺ›īňŇ–ĺŲ’Ň√ņĽ™őř◊Ô°£ĺ≤į≤«Ýľž≤ž‘ļ∂‘īňŐŠ≥ŲŅĻňŖ£¨»Ōő™–Ő∑®√ųőńĻś∂®£¨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Ķń£¨ī¶3ńÍ“‘Ō¬”–∆ŕÕĹ–ŐĶ»–Ő∑££¨ňý“‘––ő™»ň÷Ľ“™ Ķ ©ŃňőĪ‘ž––ő™£¨ĺÕĻĻ≥…īň◊Ô°£
°°°°…Ōļ£ –Ķŕ∂Ģ÷–ľ∂∑®‘ļ…ůņŪļů»Ōő™£¨’Ň√ņĽ™ĶńĽßŅŕī”‘≠÷∑«®≥Ųļů£¨“Ľ÷Īőř∑®¬šĽß°£”…”ŕ»Ī∑¶°į≥£◊°ĽßŅŕňý‘ŕĶō°Ī’‚“Ľ“™ľĢ£¨∆š…Ū∑›÷§∂™ ßļů£¨ĽßľģĻ‹ņŪĽķĻō≤Ľń‹ő™∆š≤Ļįž£¨ Ļ∆š‘ŕ»’≥£…ķĽÓ÷–”ŲĶĹņßń—°£‘ŕīň«ťŅŲŌ¬£¨’Ň√ņĽ™ĻÕ”√ňŻ»ňőĪ‘ž“Ľ’Ň…Ū∑›÷§£¨ĹŲĹęīň÷§”√”ŕ’ż≥£ĶńłŲ»ň…ķĽÓ°£“Ú’Ň√ņĽ™őĪ‘žĶń…Ū∑›÷§–ŇŌĘ «’ś ĶĶń£¨≤Ľīś‘ŕ“Ú Ļ”√ł√÷§ Ķ ©ő•∑®––ő™ļůőř∑®≤ť’“ő•∑®»ňĶńŅ…ń‹°£’Ň√ņĽ™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ňš»Ľő•∑®£¨Ķęőī∂‘…ÁĽŠ‘ž≥…—Ō÷ōő£ļ¶£¨ ۔૝ĹŕŌ‘÷Ý«ŠőĘő£ļ¶≤Ľīů°£“ņĺ›–Ő∑®Ķŕ13Őű°į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ő£ļ¶≤ĽīůĶń£¨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°Ī£¨’Ň√ņĽ™ĪĽ÷’…ů–Żłśőř◊Ô°£
°°°°Ň–ĺŲ¬Ř Ų≥∆£ļń≥÷÷ĪŪ√ś∑ŻļŌ–Ő∑®Ļś∂®Ķń––ő™£¨÷Ľ“™ňŁ Ű”ŕ–Ő∑®Ķŕ13ŐűĻś∂®Ķń∂‘…ÁĽŠő£ļ¶≤Ľīů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Ķń––ő™£¨‘Ú“≤ĺÕ≤ĽĺŖ”––Ő ¬ő•∑®–‘ļÕ”¶ ‹–Ő∑£≥Õ∑£–‘°£“Úīň£¨į—ő’––ő™Ķń…ÁĽŠő£ļ¶–‘≥Ő∂»£¨ «ĹÁ∂®◊Ô”Ž∑«◊ÔĶńĻōľŁ°£
°°°°°į∑«Ō‘÷Ý«ŠőĘ°Ī «ĻĻ≥…∑ł◊Ô∆ūĶ„
°°°°’Ň√ņĽ™įłňĶ√ų£¨»Ō∂®∑ł◊Ô£¨ĹŲ“ņĺ›–Ő∑®ŐűőńĹÝ–––ő Ĺ÷ų“ŚĶńĹ‚ Õ «≤ĽĻĽĶń£¨»ÁĻŻ…ÁĽŠő£ļ¶–‘ Ķ÷ …Ō√Ľ”–īÔĶĹ—Ō÷ōĶń≥Ő∂»£¨ĺÕ≤Ľń‹»Ōő™ «∑ł◊Ô°£
°°°°°įļ‹∂ŗ»ň»Ōő™£¨÷Ľ“™ Ķ ©Ńň–Ő∑®Ļś∂®Ķń––ő™£¨ĽÚ’ŖīÔĶĹŃň–Ő∑®ŐűőńĻś∂®ĶńĪÍ◊ľ£¨ĺÕ“Ľ∂®ĻĻ≥…∑ł◊Ô°£’‚÷÷∑®¬…“ĽĶ∂«–ĶńŅī∑®īś‘ŕőů«Ý°£°ĪĪĪĺ©∑®‘ļĶń“ĽőĽ–Ő ¬∑®ĻŔłśňŖľ«’Ŗ£¨‘ŕő“Ļķ£¨—Ō÷ōő£ļ¶…ÁĽŠĶń––ő™≤ŇĻĻ≥…∑ł◊Ô°£–Ő∑® «◊Óļů Ļ”√Ķń∑®¬…£¨÷Ľ”–∆šňŻ∑®¬…őř∑®Ķų’ŻĶń≤Ňń‹”…–Ő∑®ņīĶų’Ż°£Ķę «£¨≥…őń∑®Ķńĺ÷Ōř–‘Ķľ÷¬–Ő∑®Ķńőń◊÷Ņ…ń‹įŁļ¨Ńň Ķ÷ …Ō≤Ľ÷ĶĶ√ī¶“‘–Ő∑£ĶńŌ÷Ōů°£
°°°°ňý“‘£¨–Ő∑®◊‹‘ÚĻś∂®°į«ťĹŕŌ‘÷Ý«ŠőĘő£ļ¶≤ĽīůĶń£¨≤Ľ»Ōő™ «∑ł◊Ô°Ī£¨“™«ů∑®ĻŔŇ–∂®ń≥“Ľ––ő™ «∑ŮĻĻ≥…∑ł◊Ô£¨Īō–ŽľŠ≥÷ Ķ÷ Ĺ‚ ÕĶńŃĘ≥°£¨ Ļ–Ő∑®ňýĻś∂®Ķń––ő™ĹŲŌř”ŕ÷ĶĶ√Ņ∆ī¶–Ő∑£Ķń––ő™°£∑Ů‘Ú£¨“ņĺ›–ő Ĺ÷ų“ŚĶńĹ‚ Õ£¨ÕÍ»ęŅ…ń‹Ĺę√Ľ”–«÷ļ¶∑®“śĽÚ’Ŗ«÷ļ¶≥Ő∂»«ŠőĘĶń––ő™◊ųő™∑ł◊Ôņīī¶∑£°£
°°°°ő“Ļķ–Ő∑®ŐŚŌĶ÷–£¨–Ő∑®◊‹‘Ú∂‘–Ő∑®∑÷‘ÚŐűőńĺŖ”–÷łĶľļÕ÷∆‘ľ◊ų”√£¨ňý“‘–Ő∑®∑÷‘Ú÷–»őļő∑ł◊ÔĻĻ≥…“™ľĢĶńĹ‚ Õĺý≤Ľń‹Õ—ņŽ◊‹‘ÚĶŕ13Őű°įŌ‘÷Ý«ŠőĘ≤Ľ «∑ł◊Ô°ĪĶńĻś÷∆°£’‚“‚ő∂◊Ň£¨ĻĻ≥…∑ł◊ÔĶń∆ūĶ„£¨÷Ń…Ŕ ««ťĹŕ°į∑«Ō‘÷Ý«ŠőĘ°Ī£¨∑Ů‘ÚĹę≤ĽĽŠ“ż÷¬–Ő∑®Ľķ∆ųĶń∑Ę∂Į°£
°°°°ňĺ∑®…ůŇ–÷–£¨∑®ĻŔ‘ŕĪĽłś»ňĶń––ő™ÕÍ»ę∑ŻļŌ–Ő∑®Ļś∂®Ķń–ő Ĺ…ŌĶńĻĻ≥…“™ľĢ«ťŅŲŌ¬£¨»‘–Ž◊ŘļŌ»ęįłļ‚ŃŅ£¨Ņľ≤žĪĽłś»ň––ő™ňýĺŖ”–Ķń…ÁĽŠő£ļ¶–‘ľį∆š≥Ő∂»£¨»ÁĻŻ“ĽłŲĺŖŐŚ––ő™≤ĽĺŖ”–’ś ĶĶń«“īÔĶĹ“Ľ∂®—Ō÷ō≥Ő∂»Ķń…ÁĽŠő£ļ¶–‘£¨‘ÚłýĪĺőř–Ť∆ņľŘňŁĶń–Ő ¬ő•∑®–‘°£
°°°°Ī»»Á£¨–Ő∑®Ķŕ280Őű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◊Ô «ľÚĶ•◊Ô◊ī£ļ°į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Ķń£¨ī¶3ńÍ“‘Ō¬”–∆ŕÕĹ–Ő°≠°≠°ĪĶę“Úő™÷Ľ”–°į∑«Ō‘÷Ý«ŠőĘ°ĪĶń––ő™≤ŇĻĻ≥…∑ł◊Ô£¨ňý“‘≤Ę∑«ňý”–őĪ‘ž…Ū∑›÷§Ķń––ő™“Ľ¬… «∑ł◊Ô°£
°°°°ŃĘ∑®Ĺ‚ĺŲ
°°°°ĽĻ «ňĺ∑®Ĺ‚ĺŲ
°°°°∑ł◊ÔĪŖĹÁĪšĶ√≤Ľ»∑∂®“ż∑ĘŃň»ň√«Ķ£”«£¨‘ŕő“Ļķňĺ∑®Ľ∑ĺ≥īś‘ŕ÷÷÷÷ő Ő‚Ķń«ťŅŲŌ¬£¨Ĺę Ķ÷ …Ō≤ĽĻĻ≥…∑ł◊ÔĶńĹ‚ Õ»®ĹĽłÝňĺ∑®Ĺ‚ĺŲ£¨Ņ…ń‹ĽŠĶľ÷¬≤ĽĻę°ĘłĮį‹°£‘ŕ’‚łŲő Ő‚…Ō£¨Ļę÷ŕ∆’ĪťĶń–ńŐ¨»‘ «Ō£ÕŻ”…ŃĘ∑®Ĺ‚ĺŲ£¨“≤ĺÕ «≤Ľł≥”Ť∑®ĻŔ◊‘”…≤√ŃŅĶńŃťĽÓ–‘£¨÷ĽÕ®ĻżŃĘ∑®ĺÕĹęĻĻ≥…∑ł◊ÔĶń∂®–‘“ÚňōļÕ∂®ŃŅ“Úňō»ę≤Ņ√ų»∑£¨»√∑®ĻŔŌŮĽķ∆ų“Ľ—ý£¨÷Ľ–Ťįī’’∑®¬…ŐűőńľÚĶ•Ľģ∑÷°£
°°°° ¬ Ķ…Ō£¨łųņŗįłľĢ Ķľ «ťŅŲÕýÕýłī‘”∂ŗ—ý£¨«ß≤ÓÕÚĪū£¨≤Ľ∂Ō≥Ų–¬£¨∂ÝŃĘ∑®‘ŕĪŪ Ų…Ō”÷ĺŖ”–ľÚ√ų“™«ů£¨Õ®ĻżŃĘ∑®ÕÍ»ęĹ‚ĺŲĺŖŐŚ∑ł◊ÔĶń≥…◊Ô≥Ő∂» «ń—“‘ ĶŌ÷Ķń£¨’‚ «≥…őń∑®Ō»ŐžĶńĺ÷Ōř–‘°£‘ŕ’Ň√ņĽ™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–Żłśőř◊Ôįł÷–£¨ĺÕ–Ť“™”…ňĺ∑®ĽķĻō∂‘őĪ‘žĺ”√Ů…Ū∑›÷§◊Ô”Ť“‘Ĺ‚ ÕļÕŇ–∂Ō£ļőĪ‘ž––ő™‘ŕļő÷÷«ťŅŲŌ¬ĺŖĪł–Ő∑®ňý“™«ůĶń—Ō÷ō…ÁĽŠő£ļ¶–‘£¨‘ŕļő÷÷«ťŅŲŌ¬ĹŲĺŖ”–“Ľį„“‚“Ś…ŌĶń…ÁĽŠő£ļ¶–‘°£»ÁĻŻ≤Ľł≥”Ťňĺ∑®ĽķĻō’‚—ýĶńĹ‚ Õ»®Ń¶£¨∂Ý «ľÚĶ•Ķń“ĽĶ∂«–£¨‘ÚīňįłĶńőĪ‘ž––ő™ĺÕ «∑ł◊Ô°£’‚őř“…ĽŠ Ļń≥–©Ī唶––’Ģī¶∑£Ķń––ő™…żłŮő™–Ő ¬ī¶∑££¨Ķľ÷¬–Ő ¬īÚĽųĻż÷ōļÕňĺ∑®◊ ‘īĶńŌŻļń°£
°°°°ľ»»Ľőř∑®”√∑®¬…”Ô—‘∂‘łī‘”įł«ť◊ų≥Ų◊Ô”Ž∑«◊ÔĶńĺę»∑∂®őĽ£¨ő“√«ĺÕ÷Ľń‹“ņŅŅňĺ∑®Ķń◊‘”…≤√ŃŅ»®£¨’‚ «őř¬Řńń÷÷ňĺ∑®ń£ Ĺ∂ľń—“‘Ī‹√‚Ķńő Ő‚°£‘ŕő“√«’‚łŲ≥…őń∑®Ļķľ“£¨“™”…∑®ĻŔ“ņĺ›∑®¬…‘≠‘ÚĹÝ––ĺŮ‘Ů£¨Ķę «◊ÓłŖňĺ∑®ĽķĻōŅ…“‘Õ®Ļżňĺ∑®Ĺ‚ Õ ’’≠∑®ĻŔ ÷÷–Ķń»®Ń¶°£‘ŕ”Ę√ņ∑®ŌĶĻķľ“£¨’‚ŌÓ◊‘”…≤√ŃŅ»®ĹĽ”…∆’Õ®Ļę√Ů◊ť≥…ĶńŇ„…ůÕŇ–– Ļ£¨Ň„…ůÕŇĪō–Ž“‘»ę żÕ®ĻżĶń∑Ĺ Ĺ£¨∂‘”–◊Ô÷łŅō≥…ŃĘ”Ž∑Ů◊ų≥ŲŇ–∂Ō£¨“≤ĺÕ «»∑∂®◊Ô”Ž∑«◊ÔĶń∂®–‘°£
°°°°–Ő∑®◊‹‘ÚĶŕ13Őű°įŌ‘÷Ý«ŠőĘ≤Ľ «∑ł◊Ô°Ī£¨Ķń»∑Ĺę◊Ô”Ž∑«◊ÔĶńĪŖĹÁĪšĶ√ń—“‘√ų»∑£¨“≤ ĻŃĘ∑®°Ęňĺ∑®°Ę÷ī∑®∂ľĪšĶ√¬ť∑≥∆ūņī°£Ķę‘ŕ Ķ÷ …Ō£¨ŃĘ∑®‘ŕ’‚ņÔł≥”Ťňĺ∑®◊‘”…≤√ŃŅ»®£¨∆šńŅĪÍ «‘ŕĺŖŐŚįłľĢ…Ō ĶŌ÷≤ĽÕų≤Ľ◊›Ķń–Ő∑®’ż“Ś°£∆š÷–÷ō“™Ķńļ¨“Ś «£¨ő“√«≤Ľń‹“‘őĢ…Ł‘ŕĪĺ÷ …Ō≤Ľ”¶ ‹ĶĹ–Ő ¬÷∆≤√Ķń»ňĶńņŻ“śő™īķľŘ£¨»•ĽĽ»°ŃĘ∑®ĽÓ∂ĮĪĺ…Ūľįňĺ∑®°Ę÷ī∑®ĶńĪ„ņŻ°£∑®¬…Ī£Ľ§”¶ł√Ī£Ľ§Ķń»®ņŻ£¨»®ņŻ≤Ľ‘ŕ»ň…Ŕ£¨∂‘”ŕłŲŐŚ»ňņīňĶ£¨ňŁĺŖ”–°įŐžīůĶń“‚“Ś°Ī°£(«Ůőį£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