ûâÆÂû§äÍë¡¿»À¯í¥øÅÀÝ¢Çç§êùòýûÇÈ¢
 ýöÆŠ£ËÑ₤(0)
ýöÆŠ£ËÑ₤(0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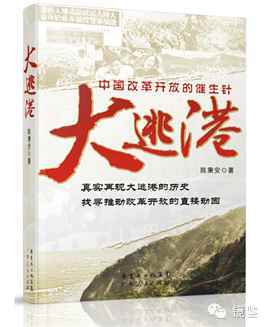
ÀÀÀÀƒïàùûþàíÝ´¿º¥òý¢À¯ƒç¥½ÀÝ¿¨øÖ¤éȘüСÜÀ¯í¥øÅÀݧþ䚧½àŠçÖ18äšÈ˜ØîÑåüСÜåš°èƒßǵƒÙ¥ûùÞòÏȘèä¥ØèºØãýØåãîõ¥¯È˜¿ÐǵòÅûþý£¢¯óðàéÀȃ祽ƊáºØ£çâȘ¢Ç¢ÇáúÅˋÀ¯ààÅáÀÝçáûâÆÂû§äÍÀÈë¡¿»À¯í¥øÅÀÝȘù«ûú¢Çç§êùòýûÇÈ¢
ÀÀÀÀÀˆÀˆÀˆÀˆÀˆÀˆÀˆÀˆÀˆÀˆ
ÀÀÀÀòúòýûÇåÖÇËÑ₤íãÅˋàùçáèþƒÙÈ¢
ÀÀÀÀØ£¤ÆøÛ¡¶È˜íãÝÔòúèŸÜÖȘáúÝÔòúüСÜÀÈùááõú¯öØçÖØ£ÇöàËüСÜȘÇÆèŸÜÖ£º°À戰ùǵ¯ëȘ80åˆàùûþÝØȘꧡ—ÑÁÅÀò݃ëç§êùëÍæÅȘØýƒëòúüøåÖçáÀ¯í¥øÅÀÝøÛçÄÀÈ¥úçûöØçÝòÝØ£ôñæÔ¿»àËȘåÖ§øëñ¤ëçõóäøÅ¢Çç§êù¤ÉÑÁüþöØØ£îªçáǵô§Æö¢ëÀÈ
ÀÀÀÀ£¿ÆÅÑÁèìàù¥úçû¥¡òÛáõú¯°èúÏèüë·Çµô§àùû¯æéèºû■öÈüíäÆ¡ÜçááúØ£á£È¢9åô°¾°—¯ÌçáÀÑ£ñú·àùöÿÀñåÆøƒýèñûêùÀÑǵäÆ¡ÜÀñØ£òÕçáæ¼íÔ°ôÝ■¯ýÀÈ°ôüàèºÑ姴¿º¤µäÆ¡ÜæÉàùò»çá¿â¥óòú100ë·ØåèüÀÈù«£¿§ýêùêÚØ£¡—ò»ƒïȘ1978áõȘèŸÜÖéˋûþàùƒªáõòíàŠø£ÆÅ134åˆÈ˜Ñ½ÑåûÌüСÜÅô§ÓçáéˋûþàùƒªáõòíàŠ¡ÔÇÿ13000¡ÜÝØÀÈ
ÀÀÀÀ1978áõ12åôȘøÅ¿ýøÅîŠòÛØ£§šà»øÅਣÃí좈ÀÈ30áõ¤µÈ˜Æ¿ºîÏíÔôÚÑÀ îé¢ùåÖÀÑöâÝ´ÀñçáØ£óˆóâôÜøÅÅÇçâȘÀ¯21òâ¥ëò¥ÆÖøÅ¿ºçá1978áõÀÝÀÈÀ¯Ø£¡—èÓ£Ãø¼ØÍ¿º¥Ø¢ˆò¥ÇÆ󧃪ø¼ØÍü·òÅ°ÀƒÙ¥ûæÔ°—êù°ÂòåÅåçáØ£ý§ÀÙÀÙù■ÇÇåšêùØ£¡—ëõà¨ý£ë˜çáâºòñÀÈøÅ¿ºçáæˆÝðØîƒÙò¿òâ§ÓçáøÄÅáѨØóÀÈÀÝ
ÀÀÀÀòâ§Óâºòñ500áõØåâÇèìÆÅçáØ£°ÀƒßÝðÆèÇù§Ø¢ˆÅ·á£ÀÈù■¿¿°èêù§þàíüСܿòòôçáØ£¡—¤õǵâºòñÝ°ƒ¯ÀÈüСÜý£åìòúÀ¯°¼Ç¯ÀÝÀÂÀ¯óšøáÀÝ£·À¯ÝÊâïÀÝÀÈ
ÀÀÀÀåÖ1997áõøÛú¯È˜üСÜçáí§ôåçÄö£òúÆèÆ¿ºø°ûþçĤëâðí§¡þƒøàñÑ´çáÀÈû⿺ø˥ơÓǵîÏâºòñîϧäòÖÑéåßóÌ(Prasenjit Duara)åÖ2009áõñÂÝÚçáÀÑüСÜƊѨîúÅôçÜ¿ºø¼ØÍȘ1941-1966 ÀñØ£öáøÅØ»ò—çáò»ƒïüåòƒÈ˜20òâ¥ë60áõǺüСÜòúùªÆÅø°ûþçÄøÅæŸÇµçáƯ¼ÇÂÝ¡£ªçÄÀÈóðÇÂê¢ÇÆ20òâ¥ë50áõǺ¤µóÖçá1.4ØÖøê1.6ØÖƯ¼èüè»ç§1967áõ10åôçá3.63ØÖƯ¼ÀÈíã¡—ò»á¢°˜¿»êùà¨Æ¿º¤ÈëãíÛöþæÉÑŸçá1/10ÀÈ££ƒð£¯ùçȘáúòÝçáüС܃ëòúÆ¿ºçáÀ¯àÀ¢Ÿ£ºÀÝÀÈÑéåßóÌàüöˆÈ˜íãØýòúöˆòýûÇÆ¿ºàùò¥øíý£å¡¡áÝðÑâýûáÈò§çá¿Ä¥■ÀÈøÝç§1967áõƯ¼ÝÃøçȘôæÑÄü·üСÜ戥ßöÈ£ºÈ˜üСÜåÖûèòɃßǵùÞòÏøÛ¤µÈ˜ýéØåÆÅüßçáÀ¯ñÇ£¼ÀÝ£þçûêùýóí±æåøöÀÈ
ÀÀÀÀâðí§ë˜òÝØýò¿üСܰèöˆûâÆÂÀ¯øàÅ·ÀÝøÅçáÝÊâïÀÈÑéåßóÌàüöˆÈ˜öˆêùö˜£ÊüСÜçáí§ôåçÄö£È˜ûâÆÂçáâ«ØÌåÖâðí§òÝàÀçûêùØ£øôȘüСÜÀ¯íãæªÝÊâïòúÝÄŊ؈¥ÃòÄæÀçáÀÝÀÈØ·öˆàÓ¿«üСÜç¿ü·¿ýýºø¼ØÍȘòóÝÄ£Ãç¥øôѨáüîúçáƒøòóÑ₤çÇÇÆѽƯüšéñøßçÜ¿ºåÖáúâÿçáâ«ØÌÀÈÆÖòúȘÀ¯ø°ûþçÄçáâ«ØÌ¢ˆò¥áèàŠÀÛæåÆèÀ₤¤ëñÝàìçáâðí§òÆدøÛøÅÀÝÀÈ
ÀÀÀÀÀ¯1997áõȘüСÜàùàÓûö°¾ÅîÀÝȘ¢ÙûÑÀÊåÙÀÊäÄâÿ(KAIMAY YUEN TERRY)åÖ11àíñÂÝÚÆÖû⿺ÀÑû¼ÅúôÜä°Ý´ÀñèüçáöáíôøÅíãîªÅÇçâÀÈíãóˆäãöˆÀÑ؈üŠíÌí»êù§ãüСÜȘÅÒ؈êù§ãù■çáâºòñÀñçáöáíôùçȘçÝáõȘçÝüСÜàù°ÂòåØåÆ¿ºø°ûþçăÆûþçáèÚñïØóûþÆ¿ºçáòݤ·È˜ù«ûúûÌêìîü¡þçáéðÑŸüßøóȘÆ¿ºû£ÆÅí颈ù¨ÝÜȘÝüƒ¿ù«ûúý£ò¶ÆÖØ£ê¼çáÀ¯ÆÂ¥ÛÀÝÀÈíãòúù«ûúåãòÉçáçÖØ£¡—èÚñïöÈ£ºÀÈà£Ñ½È˜íãøøƶûóçá¡Åƒ¾Ø£øÝîÆŽç§êù§þäšÀÈ
ÀÀÀÀý¢ñøüСÜàùÅáä˜çáý£ÝðÆŠüСÜçÄö£çáÝð£₤Åö°èüòû¼ÑåííÀÈÀ¯ÀÛí¥øÅÀ₤òô¥±øÅñÇÆ°°—çáüСÜçáèÚñïàüë˜öÈ£ºçáåÙØ·òúçÄåçí±øöÝð£₤åš°èçáÀÝÀÈíãòúû⿺îŃ¢çÄåçí±øöçáîÏíÔöçè§ÀÊ¿Ýáè(Ulson Gunnar)çáéÅÑüÀÈåÖ10åô11àíñÂÝÚÆÖà¨ú·îŃ¢ë½íƒèüçáöáíôøÅȘù«ÝÚòƒÈ˜À¯¿»àË(üСÜ)Ø£øÝòúòÉûâÆÂâ«ØÌƯüšçáȘüøåÖù■§¨¤êößØèöòçÄ£ÃòÉ秡■ÑÁçáøÅ¿ºçáƯüšÀÝÀÈöáíôàüöˆÈ˜üСÜçáèÚñïöÈ£ºýÂý£òúüСÜçá°è¿Îݣǵô§ýüò°êùÑÁèìȘѽòúùÙüøåÖíóöíæéüСܰè¿Îçá墰æÀÈáúÅˋûþø¼éèûÌêìçáîÀåþòúÀ¯¥Ã°øø°ûþçÄù¥üŠØãòѤë§ää¾È˜£¿òúåÖØ£¡—øÅ¿ºçᢷ¥ÉáÖíØç§æ奤çáÅôç᧴èÒÅåçáÑ´ö£ÀÝÀÈ
ÀÀÀÀÆŠý¢ñøüСÜàùçáèÚñïöÈ£ºüÁÑåÆÎçáȘòúØ£Åˋö¼ñ§àùò¢ÑåøÅ¿ºÃàóÞØ»ñÂçá¡þƒøøÛÝðçáý£¯ýÀÈéÎå¥îúøßÅÙ£Ãôßù¿ûâøÅ¿ÄüçøÅÅáø¼àöüáö¯(Orville Schell)éÐë˜û⿺ú¯æÉë°¢´äÄñû£ˆøÛ¤µÈ˜åÖæŸÅôØ£óÖÀÑéÎå¥òÕóâÀñåÆøƒèüñÂÝÚêùÀÑøÅ¿ºñÇ£¼ÀñØ£öáÀÈù«ùçȘ ¿»àËÝ£°óæ¼À¯ö¼ñ§ÀÝ(çáû⿺)üøåÖñÂüøæ奤ûÌêìæéØ£¡—å§âÇ姥˜òøçáƒøûÌȘ¥Çà´êÎó§¤ãí»åÖñÂèºÝð£₤Șأ¡—£¿û£ÆŤÉÑÁàùå¡Øã°ÅàüçáÝð£₤Ș¡■ý£Æûù秨íãøøàüøˆúÑàŠöØûúÆŠøÅ¿ºÇ·§£çâçáÅôñ§ò§øÛøÅêùÀÈ
ÀÀÀÀÀÑéÎå¥òÝÝ´ÀñøÅöáë½13àí¢₤ñÂêùû⿺ëùØܧ¨ƒ■öÊù¿â« K ¢ùâÙ¢ùçáöáíôȘóðÝõäãÆÅçÐѪ£ÈàùÀÑòúòݤ·ÑåøÅ¿ºÑ₤íÌ¡þçáêùÀñÀÈæ¼íÔ¢ˆû饫è§çÄÅÇçâȘÇÆüСÜç§Åô§ÛȘøÅ¿ºÑ¥åÖîüâ¼çÄî¿øóí±øöØšØÕȘѽúØù■¤ëÑÚôßù¿ÀÂØêâòÀ°₤üò¿Äü秶ûÉÀÈíãàûÅÚÑÁö¼ñ§êšç¥àùÇÆèüòâ¥ë90áõǺƒë£°ÆÅçáØ£¡—ûöüŠóóûÞêùÀˆÀˆù«ûú݃ØåöˆÈ˜À¯§´èÒÅå§ÆÇËÀÝæŸøí£Ãý£¢èÝÉûãçÄò¿øÅ¿º¡■¢ˆñéÀ¡■ûþø¼ÀÈà£Ñ½òôòçàÇúÀúÀüÁñÇȤøÅ¿ºÝðçû¡■æåÅéÀ¡■ú¢ÆýȘØý¡■ñãÝíÀÈ
ÀÀÀÀíã¤ÉàïØæàûàùêˆüŠç§À¯í¥øÅÀÝñÂèºú¯ÀÑ£ˆÑ«§øàíÝ´Àñ(9åô17àí)¢₤çúçáû⿺¿±çôîñîŃ¢ùª¡Ô¥ÑîŃ¢åÝÀÂû⿺¿ºñâý¢¿ùöò¯æ¯ŸàÞçáöáíôÀȯ毟àÞåÖöáøÅÝÚÇÿêù¥¡¤¾ë˜îªçáòÏë«¡ÅȤÀ¯öØîŃ¢øÅ¿º40áõêùȘçû°—çáÇÞ¯¡òúȘ(öµÑêøÅ¿ºçá)öòäãý£åÖøÅ¿ºèÚèüȘѽåÖÆÖöØûúæ奤ÀÈ60áõâÇȘöØûúö¼ñ§àùØ£øÝÇÆæåèÚâ«ØÌ°—ñ¢ÇÇ»øÅ¿ºÈ˜ý£òú¯îù■¢Çæ¼çøçýùíêˆçáúÝåÖûùÆîȘƒëòú¯îù■¢Çæ¼û⿺û°Øæ¤ëèäØçëÑæòçáâÇåÇÀÈÀÝæ¼íÔÑüîåȘùÌæéøÅ¿º¥äŽÃàóÞȘöØûúçÖØ£ý§ÝÐÆΡûéé°»íãÅˋÆðàùçá¥ìèÒ¤ëùóòúѽñúçáѨö¼ÀÈöØûúÝÄÅŠøÄÅôîŃ¢øÅ¿ºÈ˜ýÂàüòÑç§È˜¿ýýºç°çáë°øöíÔý££Ã¡òÅáëùüôâºòñöÒä´ÀÈ
ÀÀÀÀý£Øˆë■¥úȘ¯ô¯ëôÚí±¡ÛÀ¯îúä¨åìó§¤ãÀÝçáí§ôåƒëòúåÖíãøøòÏë«úÕżý£ÑüæäèºçáÝ°ƒ¯üôçú°ÀçáÀÈòúòݤ·öØûú¡ûàüíÌçÄüŠØ£üŠêùȘƒ¢ƒ¿òúòýûÇÇËÑ₤êùíãÅˋàùçáèþƒÙÈ¢
ÀÀÀÀòúòýûÇôÔ¥ÙåÖø¼ç¥æéù«ûúçáéÅÑüÈ¢
ÀÀÀÀû£ÆÅâðí§È˜çÝà£ý££ÃÆŧþäšûâÆÂû§äÍÑåÀ¯í¥øÅÀÝòô¥±çáíã¯ÐøÄòÆÀÈÇÆê˜óˆâÜŠ¿çáÝ´çâ¤ëñøö—øÅ¢èØå¢Ç°—ȘáúÅˋÑåÀ¯í¥øÅÀÝæÔü·¤ëÝ݃ˋÆÎÑåøÛýÔçáÇÏýãȘѥ£Ã£·ÑÁ£·èìçÄØâƒïâðí§ùªåšƒëçáØãòÑÅöä˜ÑåêÂçááÈò§ÀÈ
ÀÀÀÀÆ¿ºÀѧÞàÖòÝÝ´ÀñçáóâôÜ°óÀ¯í¥øÅÀÝòúøÅ¿ºí±¡Û25áõâÇÀ¯ûÌêìçáæŸîüøÄçáí±øöä¶í§ÀÝÀÈêÚØ£¥ØÆ¿ºû§äÍÀÑû¢àíçÓîÑÝ´ÀñçáóâôÜå·¢ðíéçħ¨òô¥±äÃè»ç§êùÀ¯èºùâÄ■¿Äçáë±ÅýÀÝÀÈÆ¿ºÀÑäˋöŸò¢Ý´ÀññÂÝÚäãöˆÀÑøÅ¿ºæ¥Ý¡èÝùâ§ÞÑšÀñçáóâôÜȘÑüîåÀ¯øÅ¿º£Ã¤êý£ÆäåËçÄí·î¿üСÜçᢿØÕ£ŸÑ₤ÀÝÀÈÀÑéÎå¥òÝÝ´ÀñçáÝ´çâ°óȘøÅ¿ºêšç¥àùÆûÆÖÆÎÑåÇùâÁòô¥±çá¿ÊƒÔÄîñÎÀÈÀу٥ûîÏàùÀñåÆøƒçáñãûÌöáíôòúÀÑç°ÆŠàùûþÑ墿ÀñçáÅîá¢ÝõäãȘÀ¯¡ÿû■ÀÝçáæøîÜå·¥¡¤¾°ð°ãåÖùªÆÅçáÝ´çâøÅÀÙÀÙ
ÀÀÀÀùÌæéòô¥±çáî什Șù«ûúçáòÆüÔ¢ˆò¥èšü·Çµô§ÀÈÀÑéÎå¥òÝÝ´Àñë½íƒ11àí¢₤çúêùäãöˆÀÑǵô§áõúÃàùë˜úÕüСÜÀ¯í¥øÅÀÝíÔêàêàÀñçáÝ´çâÀÈÝ´çâØ»ÆûØ£ö£Çµô§ÇÇØçíÔçᣯùçȘÀ¯öØûúÝÄÅŠƒ₤äÒûþø¼æˆÝð°èößí±¡ÛæÇä˜È˜ÀÝÝ´çâ°óȘƒÀ¿ÉåÖøÅ¿ºáÖçÄòÉ¿»§äÆ»çშƧæýÐøÅȘƒ½ñúùªÆÅàùÑ¥°øÆÅíãîªçá¢Çñ´È˜ç¨ù■ûúàÇÝðçûå§âÇå§óíÝÕÀÈèºÆÖèüòâ¥ë80áõǺçáàùȘåÖ¤ûâ°öŠçÓƯ¤ëéñøßöáîÏçáƯüšüô°ÊǵȘòúøÅ¿ºÑåë㢈ñéí±ýÔæŸÇµçáòÉØÌà¤äÍøÛØ£ÀÈù«ûúàÀêùÆÂöáû«È˜ò¿ÆûiPhoneȘú¯ëª¿ºëãÑà¥ìȘíãǺàù݃ÆΡûý£¢èæÒçýçÄòÉç§ûþø¼ÀÂæåÆèÝÚÇÿçàâÚüŠçáö■Ø»ÀÈòôòçÆŠøÛüÁñÇȘøÅ¿ºáÖçÄ20ÑÁùõ¤ë30ÑÁùõçáàùȘ¤ÉÑÁòú¥ãàþçáûþæÍø¼ØÍíÔȘù«ûú§ÆòÉêùí±¡ÛçáôÜò—ȘàüöˆÑåÆÖÆÅæé13ØÖàù¢ÖÀ¡ÇåÆéÆǵçáøÅ¿ºâÇùçȘö´Ø£¢èØåÝÈ£Êǵ¥ØûãòÉèÓ£ÃÑ₤çÇøÛ¢ÁȘûãòÉë㿺çÅÑåòóêÎë±ÅýçáæÕø₤ƒëòú¿ýýºç°ÀÈ
ÀÀÀÀöˆòýûÇíãÅˋáõúÃàùáÉ¿£À¯§ÆòÉí±¡ÛçáôÜò—ÀÝÈ¢öˆòýûÇǵ¥Øàüöˆø£ÆÅ¿ýýºç°ýéáÉö˜°øøÅ¿ºçáöàÑ´È¢áîç⧗§—ø£òúüþö¼ñ§û§äÍùªùççááúøøûþæÍø¼ØÍçáúÕżôÞÈ¢íãÅˋÝ´çâí»åÖØéôˋæŸøÄ؈ØýæŸøççûàËæ—çáâÚÅåñøö—ȘÆèÇùȘý£¢èÝÉûãçÄ°—üøêùÑåÝ݃ˋƒ—ýÔçáöðÑüÇÏýãÀÂÑåòô¥±Æ¯üšçáðøàƒ¢ðǵÀÈ
ÀÀÀÀƒëåÖÀ¯í¥øÅÀÝòô¥±ñÂèºçáçÖѱäšÈ˜ÆÅØ£ä¾Ýƒ¡ûØ»óÞ¡■¿Ðñ¤¿ÄæÂçáü«üÂȘàÇÝ£çÙ£₤ÇÎâÚêùÀÈ¡ªƒïòâ§ÓؽÅÅçá¿âùÐȘøÅ¿ºåÖ2014áõ9åô29àí°èöˆòâ§ÓÀ¯çÖأǵƒÙ¥ûäÍÀÝÈ£ṳ̀µÈ˜¿º¥ò£¾ÝØ£ª§ÞæÕø₤(IMF)çáò»ƒïüåòƒÈ˜øÅ¿ºÇÆ2014áõ¢ˆò¥È˜GDP§¨Çÿ17.6ë·ØÖûâåˆÈ˜°˜¿»û⿺çá17.4ë·ØÖûâåˆÀÈදǿ¤ô·êÎó§¥Ü¥óùÐȘøÅÀÂûâ꧿ºí¥òâ§ÓGDPçáñïÑŸñøÝÞöˆ16.5%¤ë16.3%ÀÈ¿ûúØý£ôÜíãê§Çµ¿º¥òæÕø₤çá¿âùÐòúñþæ¥àñȘç¨øÅ¿ºƒÙ¥ûòçêÎçáèüè»ößØèØîƒÙ嚃ëêùòâ§Ó¡þƒøøÛÝðçᣪÇÀÀÈ
ÀÀÀÀåÖíãØ£ƒÙ¥ûóÌ¥ÈçáÝ°¤µÈ˜ÆÅæéäÍøóÆŠò݃Ч½çáÝð¡ÿçáæ¼ÆûȘÆÅæéøÅ¿ºÑâäÄçáöá£₤Ǩë°çáæ¼ÆûȘÆÅæéøÅ¿ºí±¡ÛêÕ£ŸöþòççთýÔçáæ¼ÆûÀÙÀÙØ£¡—柣ªÝƒçáôÔ¥ÙòúȘåÖû£ÆÅ¡ÐúÍ°±øÅ¿º°è¿ÎȘøÅ¿ºíãÅˋáõâÇöˆòýûÇ£ÃÝÈ°øèÓ£ÃöàÑ´çáåÙØ·øÛú¯È˜ÑåøÅ¿ºí±¡Ûçáí±ýÔæÔü·¤ëüСÜú¯ƒ¯çáÇÏýãȘ¢èáÉÑ¥òúýïôòçáÀÈ
ÀÀÀÀøÅ¿ºƒÙ¥ûçáå—°Êý£òúÇÆäšèüç¶üôâÇçáȘØýû£ÆÅàùüÁÅéÀ¯°øŽ嗰ÊòúØ£øøø¼ØˆØ⢢åùó½çáùÌ£ºüøüµÀÝÀÈøÅ¿ºí±¡Û¡■ý£òúÆÅêùúÛØ夵ýéÀ¯ô·ÀÝêùöàѴȘ¡■ý£òúÀ¯Ø£øÝòåë¥Æû§ÞúÛòíô·üСÜçáàùÅáÀÝÀÈ¡á¡ÿ¢ˆñé¡íóÞý§çáòݤ·È˜°èúÏèüë·øÅ¿º¥ØëËÑ¥òúúŸçûÑÈçÝüšÈ˜èŸÜÖÆŠüСÜê§ÝÔçáòíàŠüÁýŸÇÿç§êù100ÝÑÈÀí»àÓòâ§ÓؽÅÅå—°ÊÆŠñÂí¿ö₤åÝ£ÃçáÝ´¡ÌùªîåȘÀ¯¢šùìÀ°øŽçáƒÙ¥ûå—°Êý£òúæåñÂýºèºçáȘù■ÅÒ؈أ¡—¿º¥Øí±øöêšç¥àùçá°ÊóÖ°ÅéçȘíã¡—°ÅéçÅÒ؈ØåáëÅáÀ¥ðø¤ëüøòçø¼ØÍâÇòçüøÀÝÀÈ
ÀÀÀÀÀ¯í¥øÅÀÝòô¥±ñÂ躤µÈ˜BBC¡ÐêùØ£¡—Ñ壯§Öá¢È˜úŠ°—êùÀÑçÝøÅ¿ºë°øöòâ§ÓÀñØ£òÕçáæ¼íÔôÚÑÀ îé¢ùÀÈçÝôÚÑÀüà躡í¡í§ýêùØ£ƒð؈ÆûñÂí¿çáîÜ¿ãâÇ¢ÇüСÜçáûþø¼§½°äȘø¼°øàùƒëÇ·Ñüêùù«çᣯȘ¯îù磯ç᣺£Ã¡½êùùªö§ûþø¼éèçáǺÝÚàùöÿ°ôñ§¯ýèºÀÈôÚÑÀüàèºÑåÀ¯í¥øÅÀÝ°øÆÅçá¢Çñ´¿ä࣢èØåäøôÜȘç¨ù«äð—çáý£§—òúØ£¡—¿ÜçÐȘ¡■òú¿ÜýšøÅ¿ºÀÂàüòÑøÅ¿ºçáñ§ñ´ÀÈñ§ñ´ý£ÑåȘéÅÑüƒë£ÃòÏöµÀÈ
ÀÀÀÀ§þäšæÔü·òâ§ÓçáøÅ¿ºëÑæòíÔ¤ë°èúÏèüë·çáøÅ¿ºÆö¢ëȘǽâÇçჽý£ø£òúñÂí¿°è¿«çáñøüÚȘØýòúøÅ¿ºàùÑåüøÆÅçáà¨ú·í±øöÀƒ٥ûøàÅ·çá¢Çñ´ÀÈÀ¯í¥øÅÀÝñÂèºòÝȘöØçáë˜òôîí£Ñí»åÖýÈâ«ö˜îú¤È¯ö3800ûæçáØ£æªëÙ¢µýèñû¤±áüçáØ£¥ØóµØçÀÈù»¡ÌùÔöØȘí»òúÆèÆÖíã¥ØøÅóµçáç§âÇȘ¯ýçÖù¿è§ô—óÑúŸôð¤µçáÇÍæ₤ýéÆÅêùÇÆöÇÆÅ¿»çáñÂí¿£º£ÃȘÇÍûþûúÆûèüêùøúáÉòø£ºÀÈ
ÀÀÀÀåÓåÖ2005áõȘÇÇêÂàÚòçêΡéáŸçáû⿺îÏíÔå¥èˆñ· áöƒëƒ₤¡ÌùçȘƒÀ¿ÉøÅ¿ºåÖàÚòçêÎñ§ûÌåÑý£áÉÆŠû⿺ó§óÞó§æ½È˜ç¨òúàÓ¿«¤—òÆøÅ¿ºí»åÖàÀçûç᧽í¿È˜áú§¨òúÆßÇâøÛƒìÀÈ
ÀÀÀÀòúááÅˋØ·ùÄ嚃ëêù°øŽöàÑ´çáñÂí¿È¢
ÀÀÀÀåÖÀ¯í¥øÅÀÝæŸààáøçáòݤ·È˜û⿺í±øöîÏíÔ¡Èè§çáÅôø½ÀÑí±øöøàÅ·ÆŠí±øöùËÅÁȤÇÆ¿ÊØç¡ÿû■ç§à¨ú·£₤§½°äøÅçáûþø¼ÀñèüòÅÀÈ
ÀÀÀÀ§■áõâÇȘäøôÜöáû¼ÃàóÞÆŠùËôðÀÂí±øöøóÑà¡á¡ÿÆŠîïÝ𥡤¾°èöˆ¿º¥òí±øöîϧÓçáòݼøȘíãØ£üøüµØýíÜèðêùà¨ú·ÇµÝðÑ₤øÅî¯íØÑ´ö£ÀÂä§ù¼öÇâÇçâôñçá¥ÝúÅå¡ë«ÀÈ
ÀÀÀÀÆ¿ºÀу٥ûîÏàùÀñ9åô27àíØ£óÖçáòÕóâØ»ò—êù¡Èè§çᣯȤöØûúüøåÖùª¢Çç§çáñÂèºåÖøÅ¿ºçáòôúÕȘí»òúíãøøǨë°åÖƒÙâºêùØ£¡—òâ¥ëùËôð¤µçá¡ÇÅùÀÈøÅ¿º¿ýýºç°í»åÖ£Äç§âºòñøÅàËØåøÊû¼æ奤Ș¥ÇÝÐòúû£ÆÅö¼ñ§çáûþø¼¤ëñ´øóçáǨë°ùªÇ½âÇçáØÌÇÎȘù«ûúØýáÉÇǧ´Ø£¡—ÆÅáÉêÎçáí±¡ÛÀÈ
ÀÀÀÀÀѧÞàÖòÝÝ´Àñ13àí¢₤çúçáÆ¿º§ÈúéǵîÏí±øöîϧäòÖǼö˜ âòö¼ô■(David Runciman)çáöáíôÝõäãòúÀÑ¡Èè§çáê¥øöèÓ£Ãà»ØˆùÄÀñȘæ¼íÔàüöˆ¡Èè§çá¤ùÅáôÜçÐòúȤأ¡—øàŷꥤûçáèÓ£ÃÅÒ؈໡—¿¿°è؈ùÄȤú¢í±¡ÛÀÂñ´øö¤ëûþø¼öòåÞȘà»íÔàÝØ£ý£¢èÀÈѽæŸøÄ؈çáòú؈¯îù°Å·¯ÖÑåȘûþø¼ýÂý£òúçÖØ£ö£ÀÈú¢í±¡ÛýéòúÀÈèÅöÇ£þçûòçòˋÆÅÅÏë°øöçááÉê΃맽ÅÅûþø¼£₤çáí±¡ÛößØ£â»ëãçÄÑ¥£ÃåãòÉòϯÉÀÈ
ÀÀÀÀû⿺ÀÑéÎå¥òÝÝ´Àñæ´â¡æ¼¥Ø¡Ëâÿçôô■åÖ柧■çáØ£óˆóâôÜøÅØýØ»ò—êù¡Èè§åÖ§ÆòÉù«ýèñûòÝùççᣯȤÀ¯åÖøóå¥à´êÎøÛú¯È˜òæüàÅÒ؈ýºèºà´êÎÀÙÀÙí±¡Ûý£§—§—¿Ä¤¾øóå¥È˜ØýÅÒ؈äÿˋ¯ýà¨ÝÈíüÀ£ªÇÀèÒòˋÀÂاêó¤ëñ´øöÀÈàö¤öáÉ¿£äÿˋèüò—ùªÆÅñ±öþçáòóêÎÀÝÀˆÀˆ¯■â´øÅ¿ºÀˆÀˆÀ¯Ñ¥áÉÆÛçûƒ¤à■ȘößôÜù■ûþø¼ÆŠñþÀÙÀÙÀÝ
ÀÀÀÀ¡ûà¯ùçíãÅˋîÏ躣Äç§ù«ûúçá¢öäûèüàËêùÀÈ¡Èý¥ù¿ë½íƒ10åô8àí¢₤ñÂêùǼö˜ÀʯÈÑ«ÑÄ(David Eldon)çáöáíôÀÑüСܣ¿òúøÅ¿ºçáüô篧ÞÑšôÞÈ¢ÀñÀÈæ¼íÔüÈë«åÖý£ƒû§¨âÇçáá°¡—òݤ·È˜(À¯í¥øÅÀÝçá)îÏèºûúáÉ¿£ØãòÑç§È˜àÓ¿«íãøøòôúÕ¥äŽüôàËȘù«ûú£ÃòÏàËæ奤çáöÇâÇÀÈçÝà£È˜ù«ûúØýÅÚÆÅÅùàÊ¢¥ýšØ£üô§·¯ëý¥öÊÀÂöÖ¢ùâ¥À¯ȥ¯Ø奯¤ÉÑÁóðù«çÄñ§çáÀ¯ûþø¼ÀÝÀˆÀˆáúâÿçᢿØÕ£ŸÑ₤ç§æŸ¤µÑ¥£₤öˆêùØ£°Àë§âëÀÈ
ÀÀÀÀƒëàûûâêˆèÓÑåØýûéöÈ£ºçáÝ´çââÇöˆíãØ£¿ÜçÐæ—¡—æ§é¯èÀÈíãóˆ10åô12àíñÂæåØýûéçáÝ´ç⧨2011áõåÖØýûéñÂèºçáÀ¯¯ÂâÙýÛøÛǤÀÝóÞØÍ°óæ¼òúØ£°ÀÀ¯ûö£û¤ëâùô±çáåùÑ₤ÀÝȘù■§Ãò½êùÑâýûíÔ¯Ââÿ ¯ÂýñÑéâÙ à½â«¤í33áõçáë°øöȘóÞØÍíÔûúƒ—Åá؈¯îíã¡—æŸóÑâÏçá¯ÂâÙýÛ¿º¥Ø¡áåš°èöˆØ£¡—ûþø¼çáÀÂüøǺçáèÓ£ÃÀÈÀ¯ùááõ¤µÈ˜Øýûéأ󘣚ôØÀÝÀÈ
ÀÀÀÀ(öá/ÑÀ¡í)
ÀÀÀÀÑâ¥ØåÙÇÇáÖàïȘæˆåÄúŠæÂû¼âÇæåöÂÅ鿨øÖ¤éƒç¥½(jingjianpd)
>üÁ¿ÄÅôöéȤ
>¡Ü¯áÅôö部îÀȤ
- ÀÊÀ¯îæààÀÝǤàíȤüСÜäšöáä´æÉý¢ô¥çû29.4Ñà¡Ôöô
- ÀÊ¡Ü¡Û60ØÖ§´Åôö˜¡Ü°Êâà ¤ÈݾÆé£₤ý£ø£öˆÀ¯Ç·¢´ÀÝ
- ÀÊúÍû¼§ÖóÖ¥ðüСÜѱòøôËòÅ°ˋëº °è§£ê¢íƒöàù¨ö£ò»
- ÀʃơÜǵÅÉû´í»øçñÝø°óÖ üСܤÈ¨å¯åï¿ÄÅÉû´¿ï
- ÀÊúÍû¼¥ìóÖ°˜150ë·àùÇö°—àŠ¯áûé çËàí°—àŠƒ°àùÇöÇÇÅô¡Ô
- Àʯáûéò槚À¯öá£₤ǨýËàíÀÝ¢ˆá£ ë¶û¼É¾çààööá£₤ǨýËǵò¿
- ÀÊüСܡǣŸ§ÖóÖ¥ðÀ¯Ø£úéØ£äºÀÝôûÅÅëéàùò»¥Ü¡þù¨èüè»
- ÀÊèûàÀ¡—àùæòêüëóüºýºóñ üСÜØ£ÝÈüíǺâÚÝ£ñÈ8000¡Üåˆ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