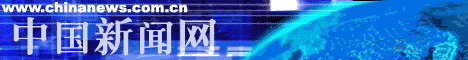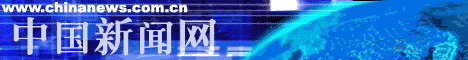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(����: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Ȩ��ע��ժ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绰:68994602)
�����й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ѽ���ݽ��ڡ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ý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ĸ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˥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ɰ��ڴ�һ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ʵ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Ҳ��ȫ�����⡣Ŀǰ���й�2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п�ɽ����2/3�����롰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440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տӣ�390������е�50�������Դ˥�ߣ�����340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Ҳ�ս���Կ�ɽ�տӵ�һ�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ǣ����йز���ͳ�ƣ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е�50����Դ�ݽ߳����У���Լ300���¸�ְ����1000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Ӱ�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ƻ��Ľ����о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ʩ�����ƽ��Ϲ�ҵ���ظ��죬��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ۺ��˲žۼ������ƣ�Ŭ����߲�ҵˮ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Ч��á���Դ���ĵ͡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١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õ���ַ��ӵ�����ҵ��·�ӡ�
����ǰ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¼ұ��Ķ���֮���ٴ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Ҳú̿��˥Ҳú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Ŀݽߣ����յ�ú����ʧҵ�ˡ�û�����أ�û���ʱ���ֻʣ�¹�ʱ��һ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л�õڶ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/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һ��Ϊ���й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Ϲ�ҵ���س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ս��ݽߵĽ��죬�Ѿ���ʧ�˵����Ĺ⻪����ҫ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ұ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ѳ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ô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ú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Ϊ��ʵ�ͽ��ĺ��ӡ�����û��˿�����ۣ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֧�Ϳ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ҽҩ�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ֳ�Ϊ�����ͥ�ĸ��ۡ���
����6��5�����绷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Բ��ǵ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ڸ�˳ȴ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��Ҫ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쵼ǩ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Ϳյĸ�˳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ش��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ƣ�ȫʡ14����ƽ��ÿ��ÿƽ�����オ����Ϊ19�֣�����˳Ϊ29�֡���˳��ȾԴ�ܶ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й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ú����¶��ú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ɽ����ռ��14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ˮ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ǡ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ĸ�Դ����Ҫ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軨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ĸ����ɴ˿ɼ�һ�ߡ�
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6��5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˳�аٻ���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⣬��֯��һ���ٶ������滭������17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£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μ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̫��Ҫ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50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5�ڶ֣��Ͻ���˰��ʮ��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ͳ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õ����ҵ��ر���ա�6��15�գ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˳��
����ʧҵ�����С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˳�еĽ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ݵ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Ư�������ۺ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ζ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İ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һ��ϴ���ݵİ�Ħʦ������10�꣬��Ůʱ������毺õ���С�仹��һ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һ�ҿ��ϸ���ڣ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Ħʦ��˵�ǰ�Ħ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ר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
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ֻҪ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ģ�����ذ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˾ͻ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俴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Ħ����Ů�˴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ڵİ�Ħ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У�ͷ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Ų���Ħ����10ԪǮ��ȫ����ĦֻҪ20Ԫ��Ҳ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20Ԫ�Ϳ������ܵ�45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Ħ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ÿ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õĹ�Ǯ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ֳɵ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찴��3��ͷ��1������3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0ԪǮ�����ٵ�һ�죬��һֻ�ֶ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С��߷߲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غ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ʱ�Ƚϡ�
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Ҳ���ܻؿ��Ϲ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ʧҵ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秵�˵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ǿ��ϵ�ͬ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ᰮ��ѧ���߿����ֻ���¾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˵ij�·�ܵ�����Ҫ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Ҫô���ȥ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4�����˳��ʧ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ݼҿ��ķ��굱���˰﹤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Ͱ��Ǵ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ʱ���Ӳ�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ˣ�û�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ڽ��ܼ��߲ɷ�ʱ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뿪��Ц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Ե���С��ֻ�ǿ�����Ц��û�б�⡣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С��ȥϴ���ݺ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ڴ�����500ԪǮ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һʱ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ֻ����һ�κ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Ӱ���ʹ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ļ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0��ĩ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39���ˣ���ȫ����λ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ʵ�ϣ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ڸ�˳����С��·�ߵ�Ů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û���ʱ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أ�Ҳû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ֻ�ò���ԭʼ�������ֶΡ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֤������һ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ʧҵ��Ա��ǰ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˳�еİ�Ħ�ݺ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С�����ʱ�𣬸�˳��ҹҹ�ϸ裬����Ϯ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ռ���ʧ��(ӦҪ����˳��һ��Ϊ����)
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300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ʷ�ϣ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(1834��)���ġ���Ҳ�Ǹ�˳����֮ʼ���京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ߡ�
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ע���ģ���˳һ��ʼ����ú���²���֮Ե���ݿ�֤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ǧ��ǰ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ס�ڽ�˳��¶��ú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з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֪��ú�ܹ�����ȡ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Ʒ��
�����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Ϊ�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ꡱ(���ꡢ���ꡢ��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ú�ֱ��ѻƬ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穣�������˥�����ò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ú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ն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ת�ø��ձ����ձ���ռ�˸�˳ú��˳�ɴ˳�Ϊ���ձ��۹���һ�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ط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Դ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ͳ�ƣ���1930�긧˳úְ̿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3����ˣ���1907���29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ú̿�Ĵ��ģ���ɣ�ʹ��˳�����˾�仯����ũҵΪ���ķ⽨����Ϊ�Թ�ҵΪ����ֳ��س��С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30���ĩ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��Χ����ĩ��4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1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˵����˳�ǹ����Ķ���ȼ��¯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˳ú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ǰ׳��ʱ��ӵ��13����ְ���ĸ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ú̿��ҵ�ij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Ϊ��˳��ע�˴������ʽ𡣽���1949�굽1985�꣬���Ҿ�Ϊ��˳�ܹ�Ͷ��40.25�ڣ���ЩǮ���൱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ĸ����ϡ�
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60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˳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˳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ǰ�С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Ӷ��Կ���ʱ���ɿ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취���ɿպ�������ɰ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е���ɾ����ķ�չ���ɿ����µķϾ�����ɱ��Ӵ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ྮû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˳�����Ϳգ��ر��³���
����2000��1��25�գ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˼ҵķ�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£�·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60�ף���40�ף���20�Ĵ�ӡ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ĸ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ﶼû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꣬��˳�н������800���ʽ𣬰Ѹ����ľ���Ǩ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ĸ���ԭ���Dz�ú���ݣ����¶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ú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Ҳ�ǵ��³��ݵ���Ҫԭ�ر�һ�³������ϵĽ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б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ĵ����¸������ֽ�11ί�ľ������ڵ�(�׳�����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Ϊ�˷�ֹ��ˮ�ͣ�����·�ϱ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ľ����ǣ���ס�ڵ���·��3��5�ײ��ȵ�·�ԣ���ΪһȺ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µ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ӵģ��Ǵӵ���ԴԴ�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ֳ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̨��ú����Ȼ�ڲ�ͣ�ؿ��ɣ���ͬʱ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10���ˮ�ݣ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ľ����Ǿ͡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Ϊ�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ã����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Ҽһ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ѷ���Σ���200���˼���һ���⡣���ݻ�ʹһ������ӱ�ŵ��˼���¯�ҿӱ�ˮ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ѱ䣬����˵��һ�����죬Ժ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͵�ϥ�ǣ�δ�ⶳǰ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ֻ�ô�С���߳�Ժ�ӡ����ڷ��ھ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ڶ��캮��̹ǵ�ʱ��һ����˯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ڸ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͡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ʹ�õĿ�ͷ�ǰ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ҵ�Ʋ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ԡ��¸�ʧҵ��Ա���족���ߵ�һ���׳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Ը���ʧҵ����һ�ʲ�������ù����뵥λ�����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Լ�һ���Ա���Ϻ����dz��ֿ�ȭ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ݽߺ������ʧҵ��Ա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ĵ��գ�ʹ��ʧҵ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˳�й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ϯ˵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Եľȼû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ǰ����ȡ100��200Ԫ�����ȼý𣬹���ֻ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ϸ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˵��ʧ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Ĺ��ˣ�û�����ؿ��֣�û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ػ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õIJ˵أ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ϻ�̨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ˮ�͵���9000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�ܳ������Ľ�60%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Щˮû�е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¥������ˮϵͳ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ܵ�ʱ�ж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ʴ���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ݰ��ͳ�ƣ�Ŀǰ�����ĸ�˳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18.41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Ĵ����8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ǹ��˼�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½�����9000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Ǩ������Ҫ7.5������ҡ�
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ɡ���ú̿�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Ķ�λת�͡�
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Σ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�Ҳ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Դ�ͳ��б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Դδ�ݽߵij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Ĺؼ����ڣ�δ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м䣬�Ĵ��ϲ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߽�Ľ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ƻ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̴�����ҹ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Żһ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ײ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Ľ�ˮһ�̲�ͣ��
����3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϶ε������С�ռ��ҹ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3��6��14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ͨ��һ�졣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9��ǰ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ͼֽ�ϵ�һ�����롣
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ؼǵ��Լ�����ӳ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ィ���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մ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ϵ��ҵ��С���Ӳ���25�꣬���ǵ����Լ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ʱ���Ѿ�64�꣬���ʸּ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ĸ�λ�����ݶ��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ʷ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ʷ�����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ʯ���һ˲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ż�þ��ͱ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ݵ�49��ǰ��1954��6�£��Ͼ���ѧ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ʾֵ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һЩ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ղ��ҿ�ʵϰ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ύ���ɳ���ϵ����һ�ɽΪ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һЩ��Χ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顣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µĹ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ʾ��ύ�˿��鱨�棬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̲��ŷḻ�ķ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1�ڶ����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ı��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ʾֵ����ӣ�ͬ��12�£����ϵ��ʾּ��ɹ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в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ϴ�ʦ�����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ʾֻ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ٴν����ص��ղ顣1955��1�£������ڽӵ����ϵ��ʾֵ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ղ�滮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꣬12��27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ʶ�����ȷ�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̲صĿ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ǰ���ƵĻ�Ҫ�ḻ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塣�����Ӵ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7�ڶ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800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��֣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͡����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»ν�ȵػ�����ʮ�ڶֵ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ۺ����ü�ֵ�ľ��ͱ��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ʱ�ĵ��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⣬����195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»㱨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�ǣ�ë�����˻㱨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ֻ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Һ�һ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С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ë��˵���Ǿ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ϵ��ʾ���1955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е��飬���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ҵ�����ﵽ30489��֡�Զ������23863.9��֡�
����1957��8�£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ʮ�˵ط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������)���ķ�չ�ƻ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ԴΪ���е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58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ϯ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Ľ���ܿ챻�����˹��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ʱ�ij�ַ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1958�ꡫ1960��䣬���蹤�����ģչ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һ�ȴ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ò���1962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1964�꣬���Ź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ȷdz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ҵ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ͻ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Ľ����漴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߶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±����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39�ꡣ��
��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衰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64��9�£�25��ijɶ�С���ӻƵ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ҵ�ˡ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Ϊ����ով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ʱ�ڵĹ��Ҷ���Щ���顣�Ƶ��α��ֻ���λ�ڼ���ijɶ���ֹܳ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ձ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С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衣1964��9��17�գ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ش�����ʱ�ѱ���Ϊ����0����˾�ィ��(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ʸֵĽ��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ַѡ���豸ѡ�ã�����ʯұ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ﶼ�����ʵģ�����û��ûҹ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ۺ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ŪŪƺ����Сɽ���ϡ����ɽ�³���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����߲�ȴ�ﵽ80���ף��dz����͡�
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65��ȫ��չ����1965��2�£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ֵ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ίԱ�ᣬ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Ȼ���߶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ұ���쵼���Ĵ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ӡ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ø���Ϊ���ɿ��С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10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˴�Լ5�������˲μ���֦���Ľ��衣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˾���Ƽ̰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μӹ�����Ԯ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س��̣����滨��һ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߲��ҵ����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ܿ࣬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Һȵ�ˮ�����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տ��ģ��ܶ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73����ƻ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ݹ���ֻ��450Ԫ�����ˣ��ƺ��Թ�ȥ�����鲻Ը���ᣬ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ط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ﻹʲô��û�С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صĸ��и�ҵ���ˣ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ϵȸ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ҵ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ȵص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1965�굽1985���21��䣬Ǩ����֦���е��˿ڴﵽ��674007�ˣ�ƽ��ÿ��Ǩ��32096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ˣ��ƺ���ȫ�Ǵ�49��ǰ�Ͼ���ѧ����ϵʦ�����Ǵ�żȻ�ĵ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Ƶĸ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Ϊˮ�����沨Ư����һҶ���ۡ�
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ʸֳ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Ҳ��1970��7��1�տ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պ�Ϊ�����ֳǵķ�չ�ṩ����Ҫ�Ľ�֧ͨ�֡�
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֦�����ڹ��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10��֣���360��֣��ֲ�260��֡�����װ��400��ǧ�ߵ��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̳��ܣ���2002��ȫ���˿ڴﵽ105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ʱ���ѳɳ�Ϊ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ø֡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ԭ�Ϻ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ع�ҵ���С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͵Ĺ�ȥ����֦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ʵ�ķ�չ��ȴ�����Ÿ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ú�����Ҫ��ֻ��֧��15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ɿڿ����(��ú����ǰ��)ԭ�ֳ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Լ���˵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ҵ֮һ��ԭ�п�7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�Դ�ݽ߶��ر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1992�갴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й�ͣת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ྭ��30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ɹ����ɵ�ʱ���Ѿ����ࡣ
����ʵ���ϣ�Ŀǰ�ڲ��Ŀ�ദ�ڼ��ѵ�ά��״̬����ԭú����һ�ֵijɱ�Ҫ110Ԫ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ȥֻ����90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Խ�ࡣ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Ŀ��θ��ֶԼ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ú��Ŀ����ú��չ�Ĵ�����䡣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700��Ԫ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ڡ�ú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ģ��ձ�ҵ�Ĵ�ѧ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İٿ�Ǯ���¸ڵľ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90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ڶ�ʢʱ�ڵľ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�������ʽְ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1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5000�¸ڻ��ָڣ���3000����ͥ���봦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7000Ԫ���ң�ԶԶ����ȫ���˾�ˮ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ɣ�Ҳ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15���ʱ�䣬Ŀǰ����Դ��̽���幤�̵��ʽ���δ��ʵ����ؽ���ԭ�пݽߺ��¿�Ͷ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ϵ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Ļ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Դ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Ωһ�ģ���֦����һ֧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ʸּ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ӵĿ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ɽ����ɽ�ȿ�ɽ����30����Ŀ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
�����ݲ��㣬��2010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û�м�ʱ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ɽ�Ŀ������ʸ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ӦΣ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Ҽƻ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ص㽨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д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ʸּ����߱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ȱ�㡣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10���ˣ�ʵ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Ҫ3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ܵ�һ��ת���ѶȺܴ��⽫��Ϊ�ʸֽ��չ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ʸ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Լ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ʸֻ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ص���Ḻ������úÿ����Ҫ֧��2800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ȷ���ı��ϣ����ʸּ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ﵽ3.4��Ԫ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ǡ���ģʽ��չ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�ۺϴ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ʸּ����dz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ľ������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ռȫ�е�60%���ҡ���һ���ʸֳ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и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ܵ�Ӱ�졣
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쾭��ת�ͣ���֦���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ͳ����߹��ġ���߳�˥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Ĺ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¡���
����6��17�գ���֦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ֹ۵�̬�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ڲ�ҵ�Ķ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Ѹ�����ҵ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ƺ��Ե�һ���ò�ҵ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չ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̹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չ֮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Ա����ĸı�ͳ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»�����֯���ƽ��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ʵ���ϸ�ļ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ʮ�ֵ�һ��һ��ת���г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ת�ͱ�÷dz����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Ϊ��ϸ�Ĺ��ˣ���ȴδ���ܹ���Ϊ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ĸ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֦���ڳ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й滮�ġ��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ķ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ҵ���й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л�����ʩ��Ƿ�˹��ࡣ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ת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ǵij������ڻ�û��ɥʧ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Ҫ��Ϊ���ύ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С�����ͷ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ȴ�����ʡ�Ĺų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Ҫ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Ȼ���о����Ĺ���Ҫ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͵���
����2001�꣬���±�ȷ��Ϊȫ��Ωһ����Դ�ͳ��о���ת���Ե㡣ȫ��50������Դ�ݽ��ͳ��У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Ҵ���һ���ɹ���ת��֮·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㸷��ģʽ�ɹ��ˣ�˭�ָұ�֤����ģʽ�Ƿ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Ŀ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ǰ��֮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/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ļ۸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ֳʳ�þ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30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ȷ���
����6��13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ũ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11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æ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ϸ�ĵذ���ͷ��С����״�û��ֿ����ֱ�װ�����ɸ�һ���ſ��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Ե����ݱ任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ɫ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˾��һԱ�����ո������йز��ŵ��ᷨ��Ӧ�ý�����ũҵ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2000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ﻹ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ú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Ƽ��ɲ���
����2001��3�£������еĶ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1��Ԫ�İ��÷��Ժ��¸ڡ��ˡ�ú���Ʋ�֮���ϵĵ�Ա��Ա����һ���¸ڿ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ת�͡��ĺ��٣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ũ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˻ص��ĸ↑����ǰ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Ϲ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ޱ��Ժ��ġ���ʱ��ú���˵Ĺ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ߵģ��ܶ���ﶼϣ���ܹ���һ���ڿ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ɷ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̲ص�ú�ڱ������˽�100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ݽߣ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ʧ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ò���ʼѰ���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ҵ���Ǹ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5��ũҵ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ݽ��ͳ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µķ�չ����ĵ�·�ϵ������ߡ�
����20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Ϊȫ��֪���ġ�ú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Ի͵���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塱�ڼ䣬�й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Ԯ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156���ص㷢չ���ع�ҵ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58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о�ռ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ݽ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ﵽ1200��֣�һ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60�ֵĿ���װ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ԭ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4Ȧ�롣
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С���úΪ�١�����ÿ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Աǰ�����١��ڸ��µ���ʷ�ϣ���ֹһ�γ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ţ����иɲ��¾���ú�Ĺ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ʮһ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ٿ�ǰ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Ϊ�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ĺ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ھͿ�ʼ��¶����һʱ�ڣ����µ�ú������Ȼֻ�����˽�һ�룬���ǽ�һ�����ɵij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Ǵ�ǰԭú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ɳɱ���Ե͵�¶���ʣ�ഢ�������̲��ڵ���700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�ڿ��ɳɱ��Ӵ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0�꣬���µľ��õ��䵽�˹ȵ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��˿ڴ���156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ռ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25%��ũ��ƶ���˿�6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0%��
����1980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ᶯ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Ժ�о�Ա½ѧ��Ϊ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븷�µ��С�
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�Ϊ��Ҫ��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⡷�ı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˵��ú��֮�ǣ���ó��桱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滹�����ȼ�֮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Ը��µ�Ͷ��88%Ͷ����ú���ϣ��ط���ҵ��ũ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12%������Ͷ�ʽṹ��ɻ��εľ��ýṹ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ý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ݲ���ֻ���쵼�㴫�ģ�Ӱ��û��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5�ꡣ
����1985�꣬������ͳ�ƾֵ�һλ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Զ���縷�µij��еĹ�ҵ��ֵ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ڣ����ʹ˸���ʱ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ݱ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ó��Ľ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Է�չ�Ͽ죬����Ϊ��ʱ����һЩ�ط��Ե���Ŀ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ݴ�������ʡҪ���ʽ�֧�֣����еط���ҵ���裬����ʡ��ƻ�����27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.7���ڡ�һŭ֮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ίд��һ���ţ�ָ�����µĽ�ѵ�ǣ�30�궼û����ʶ��ú��֮�ǵķ�չ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-����-�߳�-ή��-�ݽ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꣬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ֲ���°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չ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˺ܴ����ͬʱҲ�Ѹ���ת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һЩ�쵼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;�ܵ���Ӱ�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6���ȥ�ˣ�ʱ�䵽��1991�ꡣ����һ���ٿ����߽�ȫ���˴�һ�λ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150���ú̿���еĴ����ύ��һ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ӽ��ú̿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1991��8�£�ʱ�ι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⣬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ţ��ٳ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֮�С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ݽߵı���û��ͳһ��ʶ��ֱ��ú̿��ҵ���ĸ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Դή���ڼ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ǵ�˵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ʹÿ�꿪��1000��֣����50��û���⡱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û�з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ί�Ⱥ���1992��11�º�1997��4���·���2085�ź�721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֧�ָ���ת�͡���λ��ʱ�Ĺ���Ժ��Ҫ�쵼�ֱ��2085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ת��֮·��Ȼû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ڸ��°˽쵳���ᵽ�Ž쵳����֮�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2.6%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͡�
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ί�ḱ���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ת�͵�ָ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һ�ǰ��۹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ҵ�ϣ�ú̿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Ҫ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ڶ��ǵȴ�����֧�֣�ϣ����һЩ��Ŀ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ɼƻ����ñ�Ϊ�г����á�
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ת�͵ĺ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꣬ȴû��ʵ���Խ�չ��
����2001��5�£������оŽ쵳�����ٿ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ί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λ���֮���µ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Ե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ݾŽ쵳���ᱨ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ת�͡�ȷ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ڴ�֮ǰ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ʡ�Ը��µı��ᷨ�ǡ���ҵת�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չ�ִ�ũҵ��ũ��Ʒ����ӹ�ҵ����ȷ��Ϊ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ת�͡��ķ���֤��2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ת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Ͼ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ʺ�ũҵ��չ����Ȼ��Դ�����⣬ũҵ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ijɱ�ҪԶ���ڹ�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ת���뷨�ǣ���2002�굽2005��4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ִ�ũҵʾ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̬ũҵ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滮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��ܱ�12�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8000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50��ũҵ�����Լ�200������ֳΪ����רҵС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ת��֮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ɱ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ݿ��Դ����Ʋ��ת�͵ijɱ�����һ��ũҵ���Ľ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Ҫ2000����Ԫ��50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10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ֻ������滮�е�һ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Ͷ��֮�⣬���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ɱ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�ʧҵְ��11��࣬�����Щ�˵ľ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֪��һ�ʶ�ô�ɹ۵���Ŀ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͵���Ӧ��˵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ȡ�Ľ������ʱ�Ĺ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ܴ�̶��ϴٶ���ת�͵Ľ�չ��
����2001��8�£�����嵽�����Ӳ죬�й��쵼�㱨�˸��¼���ƶ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Сʱ�Ľ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0����̸���¡���˵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ݽ��ͳ��б�ɾ��÷���ij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漣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ץ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ᡣ8��31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Ҧ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¶Թ���Ժ���ĵĸ�л�ͼ��ܶ��ľ��ġ�3����½ӵ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ָʾ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µĹ����㱨��
����12��14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»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㱨ʱ�廰˵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㱨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ת���Ե��Ҫ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ɣ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ڹ���[2001]76���ļ��б�ȷ��Ϊȫ��Ωһ����Դ�ͳ��о���ת���Ե㡣
����2002��2��28�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11.8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000����֧�ֺ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ȵȡ�
����Ӧ��˵���Ե���е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̼ҡ�һλ���뾭��ת�����Ĺ�Ա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Ͻӵ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ѯ�ĵ绰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15��ũҵ����30��רҵ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Ĵ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�60��Ҵ�����ҵ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00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�˸��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2���ת��֮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3��3�·����˽��Եijɹ���GDP����Ϊ20.4%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ˮ�ֵĻ������¾���ת�͵Ŀ������൱�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¼ұ�ͼ�ơ����˥�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µķ�չũҵģʽ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Ҫ��ij�̶ֳ��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긷�´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꣬ȫ��600��Ķ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ʱ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ת�͵����ӣ�û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䡣ж�θ�����һְ��ǰ3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ټ��칫�ᣬ���ָ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߸��µ��쵼�����ұ�ͬ־ר�ź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ҷ��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Ҹ�ø��á���
����2003�괺�ڣ�ʱ�ι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¼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720����Ŀ��ºͿ�һ��Խ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�ת��֮·ʱ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Ϫ��˳���еĹ�Ա������ѧϰ�¼ұ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ʾ���Ѹо������Һܿ�����Դ�ݽ��ͳ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6��1�գ���ȫ����Χ�ڶԷǵ��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¼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ᳵ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ı�Ϫ�к�˳�С����У��¼ұ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ʵ�ص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˳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60%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%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¼ұ������Ӿ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Ϲ�ҵ���ص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У��dz�����עĿ���״ν���Դ�ݽ��ͳ��е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Ტ�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Ϲ�ҵ���صĸ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¼ұ�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ʱ�´���һϵ�С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ɲ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Ҫ������֯ʵʩ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ε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漰Ⱥ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ְ�ȫ��Ч�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Ҫȡ��Ⱥ�ڵ������֧�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Ҫ����Ͷ�룬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Ⱥ�����档
������Ϊ�ˣ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¼ұ�˵��
����(��Դ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2003���23�ڣ�ԭ�⣺������50��ƶѪ���С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