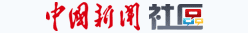°°°°»ň√«≤Ľń‹ÕŁľ«◊‘ľļī”ńńņÔņī
°°°°ľłńÍ÷ģļů£¨ĹÝ»Žīů—ßĶńŐÔľ“∂ģĶ√Ńňłł«◊ĶĪ ĪĶń∑ŖŇ≠°£Ņ…ĶĪ2006ńÍ£¨łł«◊ŐŠ≥ŲŌŽ“™≥Ųįś’‚Īĺ ťĶńńÓÕ∑ Ī£¨ňż»īőř∑®ĪŪ ĺ‘řÕ¨°£ňĶ∆ūņī£¨ňżň„Ķ√…Ō « ÷łŚ◊Ó≥űĶń°įįŽĶű◊”°Ī∂Ń’Ŗ£¨°į120∂ŗÕÚ◊÷£¨į•—Ĺ£¨Õ∑īů£¨ Ķ‘ŕŅī≤ĽŌ¬»•°Ī°£
°°°°Ō÷‘ŕŌŽņī£¨’‚łŲĻŐ÷īĶńņŌ»ň∆š Ķ‘ÁĺÕ÷∆∂©Ńň≥Ų ťľ∆Ľģ°£Õň–›ļů’ż Ĺ–ī ť Ī£¨ŐÔļťĻ‚Īš≥…Ńň“ĽłŲ°įĹŕľůĶ√ŃŖōń°ĪĶń»ň£¨…ű÷ŃĺÕѨ¬ÚŃĹ∑÷«ģ“Ľļ–ĶńĽū≤Ů£¨ňŻ“≤≤ĽŅŌīÚŅ™◊‘ľļĶńļ…įŁ°£ ģľłńÍĻż»•Ńň£¨ňŻĶń»ę≤ŅĽż–Ó”–3ÕÚ∂ŗ‘™£¨°įĺÕŌŽ”√’‚–©«ģ≥Ų ť°Ī°£
°°°°Ņ… «£¨√Ľ”–ńńłŲĪŗľ≠‘ł“‚∑—Ѷ∆Ý∂ŃÕÍ’‚—ý“Ľ≤Ņ≥§∆™°£√Ľįž∑®£¨’‚łŲ÷ōĶ£¬š‘ŕŃňŐÔľ“Ķń…Ū…Ō°£ĺ°Ļ‹łł«◊ŐŠ≥Ų£¨°į◊÷Ņ…“‘–°“ĽĶ„£¨÷ĹŅ…“‘Ī°“ĽĶ„£¨Ķęőń◊÷◊Óļ√≤Ľ“™…ĺ°Ī£¨≤ĽĻż“Úő™≥Ųįś…ÁĶń“™«ů£¨≥űłŚņÔĶńńŕ»›ĽĻ «–Ť“™īůŃŅ…ĺľű°£
°°°°īůŇģ∂ýĽĻľ«Ķ√£¨įŽńÍ ĪľšņÔ£¨◊‘ľļ√ŅŐž◊‹“™Ľ®…Ō5łŲ–° ĪĪŗľ≠’‚Īĺ ť°£ňżīÚÕ®Ńň‘≠ņī≤Ľ…ű«ŚőķĶńĻ ¬Ļ£łŇ£¨…ĺĶŰŃň–Ū∂ŗ°į”–Õ∑√Ľő≤ĶńĻ ¬°Ī°£Ņ…ĶĪŅīĶĹ—Ř«įĶń…ĺĹŕįś£¨ŐÔļťĻ‚ľÚ÷Ī∆ÝĽĶŃň°£
°°°°ňŻ÷£÷ō∆š ¬Ķō”√ļŕĪ –īŃň“Ľ∑‚–Ň£¨≤Ę«ŽņŌįť◊Ų” ≤Ó£¨…”łÝ‘ŕĪ®…ÁĻ§◊ųĶńŇģ∂ý°£
°°°°°įŐÔľ“£¨°ĪņŌ»ň“ĽĪĺ’żĺ≠Ķō’‚—ý≥∆ļŰ£¨°įő“≥–»Ō£¨ő“ «≤Ľ∂ģ”Ô∑®ļÕĪÍĶ„∑ŻļŇ£¨Ķę «ĺ≠Ļżľł ģńÍĶńŅŗ–īĺ≠—ť£¨ĽĻ «”–Ķ„÷™ ∂£¨∂ģĶ√ ų(ň‹)‘ž»ňőÔĶń”Ô—‘ļÕłŲ–‘–őŌů°£°Ī
°°°°‘ŕ≥§īÔ6“≥Ķń–ŇņÔ£¨ņŌ»ňĪß‘Ļ£¨Ňģ∂ýį—ļ‹∂ŗňż°į»Ōő™∂ŗ”ŗĶńŌłĹŕ…ĺĶŰŃň°Ī£¨°į»ÁĻŻįī’’Ī®ŅĮ‘”÷ĺĶńĻŘĶ„£¨Ť„∑Ú√«ĶńŌ¬ŃųŌį∆ÝļÕ”Ļň◊”Ô—‘ľįļ‹ń—∂ģĶń”Ô—‘(∑Ĺ—‘ĽÚī¨Ļ§ ű”Ô)£¨∂ľ”¶ł√…廕°£’‚—ýĺÕ ß»•Ńň Īīķ–‘£¨ĺÕ≤Ľ≥∆Ť„∑ÚŃň°£ ß»•Ńňņķ ∑ Īīķ∑Á∆Ý°£°Ī
°°°°ňŻ…ű÷Ń÷ ő £ļ°į»ÁĻŻ÷Ľő™”≠ļŌŌ÷īķ«ŗńÍ»ňĶń«ť»§£¨”√Ō÷īķĶńĽ™ņŲī ‘Ś£¨ń«ĽĻ”–…∂◊”ņķ ∑£Ņ°ĪňŻīÚ∂®Ńň÷ų“‚£¨’‚–© ť°į«ť‘ł≤Ľ¬Ű«ģ£¨“≤“™‘≠÷≠‘≠ő∂°Ī°£∂Ý◊ÓņŪŌŽĶń«ťŅŲ£¨ «°į◊ųő™ņķ ∑ĶńĽűŃŌį’°Ī°£
°°°°…ű÷ŃŌ÷‘ŕ£¨”ŲĶĹ«į»•ŐĹÕŻňŻĶńŅÕ»ň£¨ņŌ»ň“≤ĽŠņ≠◊Ň∂‘∑Ĺ–°…ýĶōĪß‘Ļ£ļ°į‘≠łŚ÷–∂‘»ňĶń∆ņ¬ŘļÕ÷š¬Ó£¨ľłļű∂ľ «Ť„∑Ú√«◊‘ľļňĶĶń°£Ō÷‘ŕ£¨į—ń«–©ňĶĽį»ň∂ľ»•ĶŰ£¨ļ√ŌŮ’‚–©ĺÕ «ő“◊ų’ŖňĶĶń“Ľ—ý°£°Ī“ĽłŲ∂Ő‘›ĶńÕ£∂ŔĻżļů£¨ňŻ∑ĘŌ÷ŅÕ»ň≤Ę√Ľ”–√ųį◊ňŻĶń“‚ňľ£¨ĺÕľŐ–ÝňĶĶņ£¨°įő“Ņ… «ĺ≠Ļż∑ī”“ Ī∆ŕīů√ýīů∑ŇĶń»ň£¨”––©◊ų’Ŗ¬ÓŃň»ň£¨ňý“‘ĪĽīÚ≥…°ģ”“Ň…°Į£¨Ņ…“™≤ĽĶ√°£°Ī
°°°°ĶĪŐÔľ“ī”ńł«◊ ÷ņÔ ’ĶĹ’‚∑‚–Ňļů£¨ňš»Ľ°įŅř–¶≤ĽĶ√°Ī£¨Ķę“≤ĺŲ∂®÷ō–¬ ’¬ľłł«◊ŌŽ“™Ī£ŃŰĶńĻ ¬°£—ŘŌ¬“—≥ŲįśĶń’‚Īĺ“‘ī®Ĺ≠…Ō°įőŕ„ů„ůĶńņ≠Ōň∂”őť°Īő™∑‚√śĶń ť£¨÷Ĺ’Ň≤Ę≤Ľĺę√ņ£¨––ĺŗ“≤Ī»“Ľį„–¬ ťłŁ–°°£
°°°°∂ýŇģ√«łŌ‘ŕłł«◊80ňÍ…ķ»’ Ī£¨Ĺę’‚Īĺņķĺ°«ß–ŃÕÚŅŗĶ√ņīĶń ťňÕłÝłł«◊£¨’‚ĶĪ»Ľ «ňŻ◊Óļ√Ķń…ķ»’ņŮőÔ°£ŐÔļťĻ‚ĽĻ√Ľ—ß◊ŇŃ∑Ōį◊ųľ“ĶńŇŇ≥°£¨”–Ňů”—“™ňŻ«©√Ż£¨’‚łŲįę–°ĶńņŌ»ňĺÕĹę ÷…ŌĶńņ∂≤ľīŁ∆Ő‘ŕ¬Ū¬∑Ķń ĮĹ◊…Ō£¨ŌĮĶō∂Ý◊Ý£¨”√ňś…ŪīÝ◊ŇĶńļŕ…ę¬ŪŅňĪ «©√Ż°£
°°°°…ű÷Ń£¨’‚łŲÕ»ĹŇ≤ĽŐę∑ĹĪ„ĶńņŌ»ň£¨ĽĻ≥£≥£ĶĹ–¬Ľ™ ťĶÍ£¨¬ķ◊„ĶōŅī◊Ň ťľ‹…Ōįŕ◊ŇĶńń«ľłĪĺ–¬ ť°£Ņ…»ÁÕ¨»ň√«ňý‘§ŌŽĶń“Ľ—ý£¨’‚Īĺ ťĶńŌķŃŅļ‹≤Ó£¨ňŁ√«ĶńőĽ÷√ī”√ŇŅŕ≤Ľ∂Ō«®Õý◊Ó∆ßĺ≤ĶńĹ«¬š£¨◊Ó÷’£¨Ō¬ľ‹Ńň°£
°°°°ņŌ»ň≤Ę√Ľ”–Őę∂ŗĪŪŌ÷≥Ų◊‘ľļĶńĺŕ…•£¨Ķę∂ýŇģ√«÷™Ķņ£¨°įňŻł–ĶĹļ‹ĪĮįß°Ī°£’‚–©ļŮļŮĶń ť≤ŠļÕ ÷łŚ“Ľ∆ū£¨÷Ľń‹∂—‘ŕľ“ņÔ°£ŐÔŐę»®ľ«Ķ√£¨“Ľīő£¨łł«◊ÕĽ»Ľő ∆ūňŻ «∑Ů»Ō ∂Õľ ťĻ›Ķń»ň£¨°įňÕłÝÕľ ťĻ›į…£¨÷Ľ”–‘ŕń«ņÔ≤Ňń‹Ī£īś Īľš≥§“ĽĶ„°£°Ī
°°°°’‚łŲ“ĽĪ≤◊”“≤≤Ľ∂ģÕݬÁĶńņŌ»ňł–Őĺ£¨°įŌ÷‘ŕĶńńÍ«Š»ňĺ° ż…ŌÕÝ»•Ńň£¨ļ‹…ŔŅī ť°£÷Ľļř◊‘ľļ…ķ≤Ľ∑Í Ī£¨√Ł‘ň≤Ľļ√ŇŲ…ŌŃň…ŌÕÝĶń Īīķ°£°ĪŅ…√Ľ”–»ňŌŽĶĹ£¨’‚“Ľīő£¨ÕݬÁłńĪšŃň’‚–©Ļ¬∂ņ ť≤ŠĶń√Ł‘ň°£
°°°°ĹŮńÍ3‘¬£¨‘ŕőĘ≤©…Ō”–◊Ň ģľłÕÚ∑ŘňŅĶńŐÔŐę»®°į÷ĮŃňłŲőß≤Ī°Ī£¨’‚łŲ“’ űľ“Ĺę°įņŌį÷ĶńĻ ¬°ĪŇ®ňűő™“ĽŐű100∂ŗ◊÷ĶńőĘ≤©°£Ķŕ∂ĢŐžňŻ‘ŔīőīÚŅ™őĘ≤© Ī£¨°įŌŇŃň“ĽīůŐÝ°Ī£¨’‚łŲ∆’Õ®ņŌ»ňĶńĻ ¬“—ĺ≠ĪĽ◊™∑ĘŔţ1000īő£¨∂Ý∆ņ¬Ř“≤“—ĺ≠Ŕţ500Őű°£
°°°°’‚łŲ°įĻŐ÷ī∂Ýĺů«ŅĶńņŌ»ň°ĪĶńĺ≠ņķŃÓÕÝ”—√«ŖŮ–Í°£”–»ň»»–ńĶōĹ®“ť£¨°į◊™łśń„łł«◊£¨ĺę–ńĪ£īś◊ ŃŌ£¨Ĺę◊ ŃŌ∂ŗŅĹĪīŃĹ∑›°£”√∑Ĺ—‘’ś Ķľ«‘ōĶ◊≤„…ķĽÓ…ÁĽŠÕÚŌů“‚“Ś÷ōīů£¨Ļ¶ń™īů—…°£°Ī“ĽłŲĻ„∂ęĶń°į80ļů°ĪŐŠ≥Ų£¨°įŌŽ÷ß≥÷“ĽŌ¬£¨≤Ľ÷Ľ «¬ÚĽōņī◊Ųįŕ…Ť£¨∂Ý «»Ō’śĶōŅī“ĽŌ¬£¨’‚ «“ĽłŲ»ň“Ľ…ķį°£¨∂ŗ’šĻů°£°Ī
°°°°ņŌľ“ĺÕ‘ŕ÷ō«žĶń»ňňĶ£¨√ś∂‘’‚Īĺ ť∑¬∑ū°įŅīĶĹŃňĻ ŌÁ£¨łŖłŖĶń≥ĮŐž√Ň£¨ľ§∆«ĶńŃĹĹ≠Ľ„°Ī°£‘Ýĺ≠Ķ«…Ō√ņĻķ°∂ Īīķ°∑÷‹ŅĮ—«÷řįś∑‚√śĶń«ŗńÍ◊ųľ“īļ ų£¨“≤‘ŕĶ»īżŃň13Őž÷ģļů÷’”ŕ¬ÚĶĹŃň“ĽĪĺ°£°įŃÓ»ňĺīŇŚ£°°Īňż”√◊‘ľļĶńļŕ›ģ ÷Ľķ∑Ę≤ľŃň’‚—ý“ĽŐűőĘ≤©°£
°°°°°į…Ōļ£√‘ļżŇģ«ŗńÍ°Ī“—ĺ≠∂ŃŃň“Ľ≤Ņ∑÷£¨ł–ĺű’‚°įĺÕŌŮÕ‚∆Ňłķő“–űŖ∂ĶńĻ ¬“Ľ—ý£¨Ō£ÕŻń‹”–łŁ∂ŗ’‚—ýĶń ť£¨»ň√«≤Ľń‹ÕŁľ«◊‘ľļī”ńńņÔņī°Ī°£